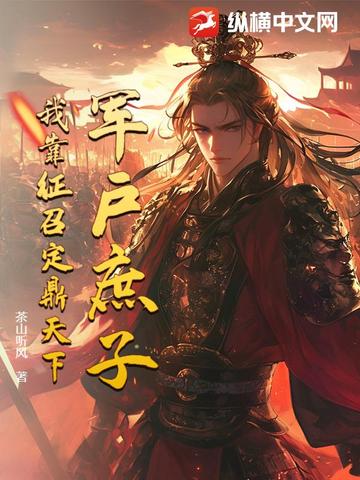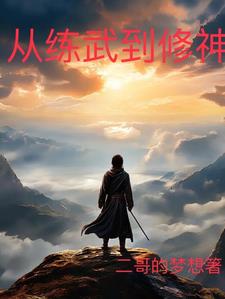第217章 资源汇流:两洲动脉与未雨绸缪的储备
红鲑河的冰刚化透,北美钢铁带的第一列“万吨钢车”就鸣笛启程了。这列车头裹着铁皮(防风雪),挂着二十节车厢,每节都装着硫磺钢锭,车身上刷着醒目的红漆——“大明北境”四个字在阳光下发亮。铁轨一路向南,穿过绿屏山的隧道,直奔新明区,再转船运回大明本土。
“这趟车够造十艘钢舰。”李匠头站在站台,看着车轮碾过铁轨的火花,对林远说。他身后的高炉群正喷着浓烟,五座炉子轮班转,煤铁混炼的配比早已精确到“每斤煤配三斤铁矿”,炼出的钢不仅韧,还带着淡淡的蓝色(硫磺钢的标志),大明工部的回信里说“此钢可造炮管,射程比旧铁炮远半里”。
南美资源腹心的“橡胶长龙”也动了起来。亚马逊河上,蒸汽船首尾相接,每艘船的货舱都堆着压成方块的橡胶(比散装多装五成),秘鲁部落的青年站在船头,用刚学的汉语喊号子:“橡胶硬,换钢锭,两洲好,不分家!”这些橡胶运到北美化工带,一半做成电缆绝缘层(铺两洲电报线),一半和硫磺反应成硬橡胶,做成钢舰的防水塞——比木塞耐用十倍。
两洲的“资源账”算得越来越细。吴兑在连湾港建了“两洲交易所”,黑板上实时写着比价:“一吨硫磺钢=五担橡胶=二十斤白银=百石稻米”,移民商人用算盘算,部落首领用绳结记,却算得一样清楚。有个黑松林部落的老人,用十张海獭皮换了半吨钢,打了二十把精工斧,再换给南美部落,一转手就赚了五担橡胶,成了交易所的“活算盘”。
为备战的储备库在隐秘处动工。林远让人在铁脊山的山洞里,建了“钢料库”(藏着千吨硫磺钢,洞口伪装成普通矿洞);在南美安第斯山的山谷,挖了“橡胶窖”(用石板铺底防潮,存着三年的橡胶量);连电报线都备了“复线”——主线路被切断,备用线能在半个时辰内接通,线头藏在树干里,只有高级匠人才知道位置。
“不能等打仗了再着急。”林远对赵武说,指着地图上的储备库标记,“这些东西,平时藏着,用时能救命。”赵武让人在储备库周围布了“三重哨”:明哨(印第安营士兵)、暗哨(部落猎人,懂伪装)、机哨(触动会响的铜铃绳),连飞鸟飞过都能惊动。
两洲学堂的“战争课”很特别。先生不教冲杀,只教“资源调配”:“若钢舰被打坏,需多少天从储备库调零件?”“橡胶线断了,用什么替代?”少年匠师班的铁蛋算得最快,他说“用钢缆裹棉布(浸过桐油)能临时当电缆”,这法子后来真被用在一次暴雨冲断电报线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2页
相关小说
- 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茶山听风)的经典小说:《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最新章...
- 611379字07-26
- 从练武到修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二哥的梦想)的经典小说:《从练武到修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548673字07-25
- 第六办花的誓约
- 17098字07-25
- 你说相信科学,自己御剑飞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醉逝烟花雨)的经典小说:《你说相信科学,自己御剑飞天?》最...
- 743419字07-26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946569字07-25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