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女子出门是很难的
令”“尚宫局”,全部职责就是管理女性宫人——她们不仅不能随意走出寝殿,就连信件都要通过内侍或女官转交。
皇后、妃子,哪怕再受宠,也需要“召见”制度,非经允许不得出宫一步。就连临时迁宫、避暑搬迁,都要单独列车、设专队护送。
同样,王公贵族的女眷也是如此。王府内宅常常有“女墙”、“影壁”,甚至院墙上加盖“女不出门”的石雕文告。到了清代,八旗贵族女子常年居住在“闺房”,即便嫁人,也不一定能立刻“出嫁”住进夫家。
上层女子的出门自由,甚至比农妇还受限制。她们有身份,却也因此被束缚得更深。
当然也有女性出现在市井街头,那多数是因为家贫无奈。
低阶层女子,如农家女、女仆、寡妇,确实可能承担卖菜、担水、送饭等任务。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有“自由”,而是她们“无可选择”。宋代一位文士在《笔谈》中就曾说:“市井妇多劳,而言语不敢稍高。”就是说,即使这些女子出门谋生,也要尽量“悄无声息”,免得惹人非议。
清代地方志也记载,女子“若非寡困,不宜贸易”。在正统的观念中,女子经商是“伤风败俗”,即使偶有例外,也要被贴上“迫于无奈”、“守节经营”的标签。
她们不是自由地出门,而是带着羞耻与危险,在社会边缘勉强求生。
古代文人极爱描写“贞女”——守节、守门、不见外人、不出家门,被赞为“冰清玉洁”;反过来,“出门女子”则多被塑造成“荡妇”或“红粉祸水”。
《聊斋志异》《世说新语》《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逃不出这个二元对立:你若出门、说话、接触男性,就注定会被“描黑”。
这种文学形象一再加深社会偏见,使得“贞节”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家族荣誉、社会标杆。甚至地方上建“贞节牌坊”,对出门女子就是无形的警告。
这类文化压力,远比明文律法更可怕。
除了宗族与礼教的束缚,古代女子还要面对来自法律制度本身的性别歧视。别以为官府公正严明,事实上,法律对女子的惩处不仅更重,而且更羞辱,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不是“公平执法”,而是“维护礼法”。
先说一个现象:同样是“私奔”,男子通常会被斥为“轻佻”“不敬父母”,但女子往往直接按“淫奔”“失节”处理,有时还会被冠以“贱行”,轻则鞭笞驱逐,重则活活打死。为什么?因为她“坏了家门名声”“败坏纲常伦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
- 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章节目录,提供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的最新更新章...
- 1784408字07-23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快穿之炮灰男配在线打脸
- 快穿之炮灰男配在线打脸章节目录,提供快穿之炮灰男配在线打脸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037981字07-22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章节目录,提供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246299字07-24
- 四合院:何雨柱顽强成长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戒色)的经典小说:《四合院:何雨柱顽强成长》最新章节全文...
- 439495字07-25
-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
-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章节目录,提供[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606830字07-23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965/64965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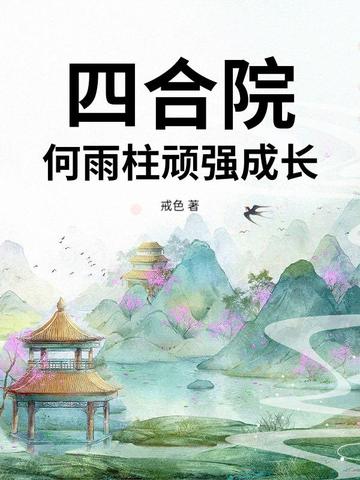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281/64281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