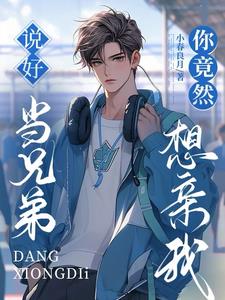第195章 烽火川魂:锦江潮涌归故里
,趴在地上。炮弹呼啸着飞来,震得地动山摇,泥水溅了他一脸。他摸出信纸,边角被弹片划破了,"鸳鸯"两个字缺了半边,像被生生拆开的一对。
"掩护伤员!"连长的吼声传来。王文书抓起步枪,跟着战友往侧翼冲,怀里的信纸硌着胸口,像块发烫的烙铁。他看见个新兵被炮弹掀起来,蓝布衫像片落叶,飘落在泥里,手里还攥着封没写完的信,字被泥水糊成了团。
激战中,王文书的胳膊被流弹打中,血顺着袖子往下淌,滴在信纸上,晕开一片红。他靠在断墙边,继续写,字迹越来越歪,像喝醉了酒:"秀莲,吾恐不能归。家中诸事,劳你多担待。吾儿......"后面的字没写完,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猛地把信纸塞进锦帕,紧紧攥在手里。
打扫战场时,卫生员从他怀里掏出锦帕,信纸已经被血浸透,只有"勿念"两个字还能看清,像句永远说不完的话。后来这封信被辗转送回广安,秀莲把它缝在儿子的襁褓里,锦帕上的鸳鸯,只剩一只孤零零的,望着西南方向。
儿子王念军长大后,在襁褓里发现这封信,血字已经变成了深褐色。秀莲摸着信说:"你爹的字,是想把咱娘俩,刻在心里。"多年后,王念军成了老师,教孩子们写字时总说:"字要写得正,像咱四川人的骨头;字要带着暖,像咱四川人的牵挂。"
四、灶台等待:温着思念的腊肉
1943年冬,四川自贡的一间茅屋里,李婆婆正往灶膛里添柴。松木柴"噼啪"地响,火苗从灶口窜出来,舔着锅底,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晃动的念想。
锅里炖着腊肉,是去年杀的年猪,最肥的那块。李婆婆用筷子戳了戳,肉皮已经软了,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绕着房梁转,像在找个出口。她对着空灶房说:"三娃,快熟了,你最爱吃肥的,娘给你留着,肥的香,能顶饿。"
三娃是她小儿子,李存厚,出川五年了,只回过一封家书,是1939年从湖南寄的,字歪歪扭扭,像他小时候爬的字:"娘,勿念,儿在前线好,能吃饱,年底或可归。"李婆婆把信裱在墙上,每天都看,纸已经发黄,边角卷了边,上面的"归"字,被她的手指摸得发亮。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灶台上摆着个粗瓷碗,碗里是炒花生,壳上沾着泥土——跟三娃走时带的一样。李婆婆每天都炒一碗,说"等三娃回来,就能吃新鲜的"。有次邻居张婶来借酱油,看见花生说:"三娃怕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兄弟装醉咬我喉结后,他哭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春良月)的经典小说:《兄弟装醉咬我喉结后,他哭了》最新章...
- 455489字06-23
- 崩坏:高级僚机不会被美少女包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灰锦鲤)的经典小说:《崩坏:高级僚机不会被美少女包围》最...
- 717540字07-17
- 废土第一卧底
- 废土第一卧底章节目录,提供废土第一卧底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25440字07-18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章节目录,提供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808924字07-18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章节目录,提供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的最新更新...
- 1456038字07-18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