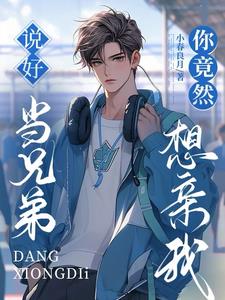第195章 烽火川魂:锦江潮涌归故里
一发炮弹吞没,手里的陶碗飞了起来,碗底的"家"字在火光中闪了一下,然后碎成了片。
"跟俺冲!"李灶保拽起王幺妹,自己抓起步枪,冻裂的手扣动扳机,子弹打在日军的钢盔上,"当"的一声脆响。他不知道自己打没打中,只觉得热血往头上涌,像盐井里沸腾的卤水,烫得他忘了疼。
激战过后,山坳里的火还在烧,只是添了些新柴——士兵们的遗体。王幺妹在雪地里找到李灶保,他怀里还抱着半罐盐菜,伤口的血冻成了暗红,像块凝固的胭脂。"灶保哥,"娃娃兵哭着摇他,"你说的红薯,俺还没吃着呢......"
后来打扫战场的山西老乡,把李灶保的陶罐碎片埋在火边,撒了把盐。老乡说:"四川娃爱吃盐,咱这儿的土,得让他尝着味。"每年下雪时,山坳里总像有盐香飘,混着松柴的烟,像有人在煮一锅永远吃不完的盐菜。
三、战壕家书:写着牵挂的血字
1940年春,长沙城外的战壕里,月光像层薄霜,铺在泥泞的地上。王文书借着月光写信,信纸是从烟盒上撕的,背面还印着"红锡包"三个字,笔尖蘸着口水,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用尽了力气。
他本名王敬书,广安人,读过三年私塾,在部队里当文书,负责写家书、记伤亡。士兵们都叫他"王文书",说他的字比秀才写得还俊。此刻他的右手缠着布条,是昨天埋地雷时被碎石划的,血渗过布条,在信纸上点出个小小的红痕。
"秀莲吾妻,"他写下这行字,笔尖顿了顿,想起秀莲织蜀锦时的样子。她的手很巧,竹梭在她手里飞,锦面上的芙蓉花就像活的,"前日打退鬼子一次,吾安好,勿念。汝寄来之布鞋已收到,鞋底纳了三十六针,厚实,踩在泥里不滑,比军靴好......"
战壕外传来虫鸣,"唧唧"的,混着远处的炮声,像支没调子的歌。王文书摸出怀里的锦帕,是秀莲送的,上面绣着鸳鸯,一只翅膀已经磨没了。他把锦帕铺在膝盖上,对着月光看,仿佛能看见秀莲坐在织机前,额头上渗着细汗,说"鸳鸯得成对,人也得团圆"。
"吾儿若长,"他接着写,笔尖在纸上抖了抖,"教其识字,勿学吾辈,只会打仗。告诉他,爹爹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长大,看着他读'仁义礼智信'......"写到"信"字,突然停住了——他已经一年没收到秀莲的信了,不知道儿子是否平安,是否还记得爹爹的模样。
旁边的机枪手突然低吼:"鬼子来了!"王文书赶紧把信纸往怀里塞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兄弟装醉咬我喉结后,他哭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春良月)的经典小说:《兄弟装醉咬我喉结后,他哭了》最新章...
- 455489字06-23
- 废土第一卧底
- 废土第一卧底章节目录,提供废土第一卧底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25440字07-18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章节目录,提供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808924字07-18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崩坏:高级僚机不会被美少女包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灰锦鲤)的经典小说:《崩坏:高级僚机不会被美少女包围》最...
- 717540字07-17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章节目录,提供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的最新更新...
- 1456038字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