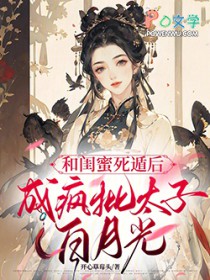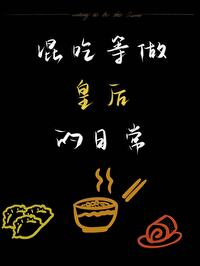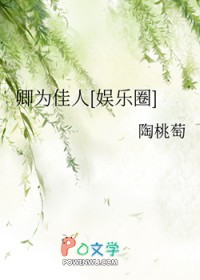第192章 蜀地造物记:从盐井到星穹的匠心长歌
“一根线在经线上走三步,突然拐个弯,就织出了一片云彩——跟咱成都的巷子似的,走着走着就撞见惊喜。”有个学服装设计的女生,蹲在展台前临摹纹样,笔尖在速写本上勾勒的弧度,竟和织锦上的龙尾一模一样。
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青神竹编展区的“竹丝扣瓷”。一只竹编茶杯套,细如发丝的竹丝紧紧裹着白瓷,竹节的纹路与瓷杯的弧度严丝合缝,晃一晃,竹丝贴着瓷面轻轻响,像春蚕在桑叶上踱步。“编这个得屏住呼吸,”讲解员说,“竹丝太脆,力气大了会断;太轻了又贴不牢,就像四川人处世,要的就是个‘恰到好处’。”一位外国游客举着相机拍了又拍,嘴里念叨着“magic”,他大概不懂,这“魔法”里藏着多少个在竹林里劈篾到深夜的夜晚。
展厅的出口处,摆着张长条桌,几位老匠人正在现场演示。自贡的罗师傅用小锅熬着卤水,蒸腾的白雾里飘着淡淡的咸香,他不时用竹勺舀起卤水,看盐花在勺底结晶:“要等这盐花像雪花一样飘,才算熬成了。”荣昌的陈婆婆捏着陶泥,手指翻飞间,一个小小的陶辣椒就有了模样,她递给围观的孩子:“拿着玩,咱四川的辣,得从娃娃抓起。”青神的王老汉坐在竹凳上编竹篮,竹篾在他膝间游走,像条绿色的蛇,他抬头对年轻人笑:“编竹器跟谈恋爱一样,得有耐心,急不得。”
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刚买的蜀锦书签,追着胡素芬的孙女问:“阿姨,这上面的芙蓉花,是不是跟锦江边的一样?”姑娘蹲下来,指着书签上的纹路:“是啊,织的时候就想着,要让芙蓉花永远开在丝线上,不管刮风下雨。”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头,把书签夹进绘本——那本绘本里,正画着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树上的太阳鸟,翅膀上的纹路竟和蜀锦的经纬有几分相似。
闭馆的铃声响起时,老匠人们收拾着工具,罗师傅的小锅里还剩着最后一点盐,像碎银子;陈婆婆的陶泥用湿布盖着,明天还能接着捏;王老汉的竹篮编了一半,放在墙角,像只待飞的鸟。讲解员锁展柜时,发现玻璃上印着自己的影子,与展柜里的老物件叠在一起,突然明白:所谓匠心,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把日子过成手艺的模样。
走出博物馆,暮色已漫过锦江边的吊脚楼。茶馆里飘出盖碗茶的清香,路边小贩的糖油果子滋滋作响,穿汉服的姑娘们举着灯笼走过,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远处的廊桥上,有人在唱川剧,高腔穿透夜色,像根无形的线,一头拴着三星堆的骨笛,一头连着年轻人手机里的流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章节目录,提供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的最新...
- 762398字07-18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章节目录,提供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808924字07-18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章节目录,提供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476108字07-18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章节目录,提供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的最新更新...
- 1456038字07-18
- 卿为佳人
- 卿为佳人章节目录,提供卿为佳人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406508字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