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剑笔同辉:张爱萍诗词里的山河与锋芒
风沙把太阳磨成了毛玻璃。张爱萍踩着滚烫的沙子勘察试验场,皮鞋底烙得滋滋响,他却对身边的科学家说:"这里的月亮比别处亮,适合写诗。"后来真有了《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头顶烈日,明月做营帐"的句子,成了科研人员最爱哼唱的歌谣。有次他听见几个年轻技术员在帐篷里唱这歌,跑进去纠正:"‘饥餐沙砾饭’的‘砾’字要唱得重一点,才有嚼头!"
那时候的核试验基地,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夏天帐篷里能煮鸡蛋,冬天冻得钢笔都不出水。张爱萍和科学家们住在同一排土坯房里,同吃窝窝头,同睡硬板床。有次沙尘暴把屋顶掀了,他和大家一起用石头压住油布,嘴里还开玩笑:"这是老天爷在给咱们的诗谱曲呢!"当晚他就写了首《沙暴》:"黄沙万里压城来,乱石飞旋打帐开。莫道戈壁无乐趣,天公为我送歌来。"第二天贴在食堂门口,逗得大家直乐。
1964年10月16日,蘑菇云在戈壁升起时,张爱萍站在观测站里,看着那朵"万丈长龙",突然想起少年时写的"州河狂怒",只是此刻的波澜,早已跨越了山河。他身边的科学家们相拥而泣,他却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写完把笔一扔,也加入了欢呼的人群。庆功宴上,他把这首诗念给大家听,有人提议干杯,他却说:"这杯酒,敬那些没等到今天的战友。"
"文革"开始后,张爱萍被关进了监狱。左腿被打致残,他却在烟盒纸上写满了对核试验的思考,其中有句:"纵使身残志不残,还将神剑刺苍天。"看守发现后抢走了烟盒纸,他就把诗句默念在心里,每天背一遍,怕忘了。1975年复出那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被迫害的科学家,握着邓稼先的手说:"我们的诗还没写完呢。"
1980年5月,洲际导弹横跨太平洋的那一刻,指挥大厅里的掌声震落了窗台上的灰尘。张爱萍挥笔写下"东风怒放,烈火喷万丈。霹雳弦惊周天荡,声震大洋激浪",墨汁溅在军装上,他却浑然不觉。有人说这诗太"硬",他笑答:"导弹是铁做的,诗也得带着钢味儿。"当晚的庆功宴上,他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给大家讲1925年写"踏着血迹救中华"的往事,说:"那时候哪敢想,咱们能把‘东风’送到太平洋去!"
四、诗为号角催征人
1941年的淮北平原,麦浪翻滚着涌向天际。张爱萍率领新四军九旅在津浦路东开展游击战,白天隐蔽在青纱帐里,夜晚就摸进敌营袭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
- 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章节目录,提供和闺蜜死遁后,成疯批太子白月光的最新...
- 762398字07-18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
- 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章节目录,提供混吃等做皇后的日常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476108字07-18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
- 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章节目录,提供穿成六零极品炮灰,我绝不洗白的最新更新...
- 1456038字07-18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
- 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章节目录,提供娇媚天成:冷面君王心尖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808924字07-18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865466字0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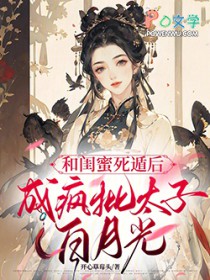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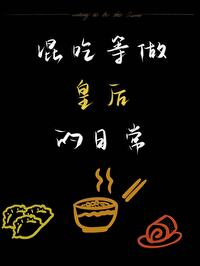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60/62760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