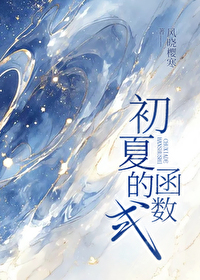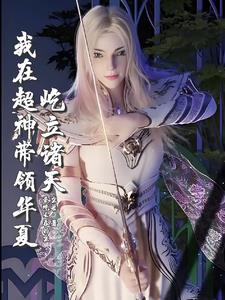第166章 元稹: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
在通州的第三年,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他在州河南岸的青爱山(今翠屏山)选址,亲自督导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取名“戛云亭”。“戛云”二字,取自“戛然独立于云端”之意,既是对亭子地势的描述,也暗含着他的精神追求——即便身处蛮荒之地,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
戛云亭虽简陋,却是元稹观察通州、思考人生的“精神高地”。他常在此登高远眺,俯瞰州河如带,远眺大巴山如黛,写下《戛云亭》一诗:“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有浮云横碧落,更无幽恨到黄尘。”诗中没有贬谪的怨怼,只有对天地广阔的感悟,这种“超越苦难”的心境,与他早年的愤懑形成鲜明对比。
在戛云亭,他还完成了《连昌宫词》这篇长篇叙事诗。诗中借连昌宫的兴废,回顾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兴衰,“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通过今昔对比,反思安史之乱的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视角,正是他在通州沉淀后的思想升华。
除了作诗,元稹还在戛云亭接待来访的友人。当地学子听说这位“京城来的诗人”博学多才,常来请教,他总是耐心讲解,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为学子购置书籍。有一次,一位老秀才来请教《诗经》,他与之谈至深夜,临别时赠诗:“衰容不称君,清风满敝庐。”这种与百姓的亲近,让他逐渐融入通州的生活。
3. 与白居易的“云端唱和”
通州的岁月虽苦,却因与白居易的书信往来而多了几分温暖。当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二人虽相隔千里,却以诗唱和,“每得一诗,即夜起盥栉,张灯细读,倦则拥衾而卧,梦中犹吟哦不止”。
元稹在《酬乐天频梦微之》中写道:“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看似“不梦君”,实则因思念太深而不敢入梦,这种“反语抒情”的笔法,让白居易读罢“涕泗横流”。白居易则回赠《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二人的唱和,被后人辑为《元白唱和集》,成为中唐诗坛的一段传奇。
这些书信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思想的碰撞。他们讨论诗歌创作,元稹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强调诗歌的情感与现实意义;他们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元稹在信中写道:“通州虽远,然百姓疾苦,与江州何异?”这种对民生的共同关注,让他们的友谊超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865466字07-21
- 攻略成功后,被疯批缠上了
- 415606字07-19
-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
- 2740951字07-19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18771822字07-21
- 初夏的函数式
- 初夏的函数式章节目录,提供初夏的函数式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31514字07-21
- 超神:我以虚空万藏解析诸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云吞的京京兽)的经典小说:《超神:我以虚空万藏解析诸...
- 636518字07-23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60/62760s.jpg)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75/62775s.jpg)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3/63060/63060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