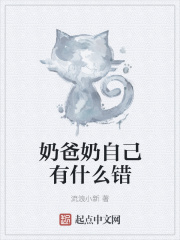第165章 巫山云水记:大地与江河的千年情话
底包着铁皮,船头装着"防撞木",遇到礁石能硬生生"顶"过去。这种船的梢公都是"老江湖",能在浪头里找准航线,他们说"滩船不是在走水,是在跟礁石打架"。1950年代,还有滩船在西陵峡航行,船上的纤夫最多时达三十人,喊声震天,船却像被钉在水里一样,一寸寸往前挪,那场景,是三峡航运最壮烈的画面。
如今,这些木船大多进了博物馆,但在巫山神女溪的支流里,还有渔民划着小独木舟捕鱼,船桨入水的声音,还和千年前一样清脆。
2. 纤夫:用脊梁丈量江河的人
在机动船出现前,纤夫是三峡江面上最动人的风景。他们光着脊梁,拉着粗如手臂的纤绳,在滚烫的岩滩上、陡峭的崖壁间,一步步把船"拽"过险滩。这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汉子,用脊梁丈量着江河的长度,用脚印在三峡的岩壁上刻下了文明的印记。
纤夫的"行头"很简单:一条短裤,一双草鞋,头上裹着粗布帕子。夏天防晒,冬天挡寒,帕子脏了就在江里涮一涮,拧干了再用。最特别的是"纤搭子"——一块垫在肩上的厚帆布,上面缝着补丁,浸过汗、泡过雨,硬得像铁皮,却能在拉纤时减轻绳索对肩膀的摩擦。老纤夫说,好的纤搭子要"三年养",越用越贴身,"就像第二层皮肤"。
拉纤的"规矩"比山还重。过险滩时,所有人必须步调一致,由"头纤"喊号子定节奏,其他人跟着迈步,不能快也不能慢,"一步错,步步错,船就可能撞礁"。头纤都是经验最丰富的老纤夫,不仅要力气大,还要眼观六路——既要看着前面的路,又要留意船上梢公的手势。在青滩的"纤夫石"上,能看到深浅不一的脚印,最深的有3厘米,那是几十年间纤夫们踩出的"路"。
最苦的是"逆水拉纤"。尤其是在瞿塘峡,江水湍急,船根本开不动,全靠纤夫拉。三十多人的纤队,像一条黑色的长龙,趴在滚烫的岩滩上,纤绳绷得笔直,勒进肩膀的肉里,留下深深的红痕。有人受不了疼,会喊几声号子发泄,号子声混着喘息声,在峡谷里回荡,像一首悲壮的歌。有位老纤夫回忆:"拉完一趟纤,肩膀像掉了一样,吃饭都拿不起筷子,但看到船过了滩,心里比啥都踏实。"
纤夫们的"智慧"藏在细节里。他们能根据江水的颜色判断深浅:"江水发绿,底下有礁;江水泛黄,水深够航";能根据浪花的形状辨险滩:"浪花打旋,必有暗礁;浪花成线,是条好道"。这些口耳相传的"水文谚语",比任何航图都管用。他们还会在常走的路线上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2页 / 共17页
相关小说
- 天龙人们强取豪夺的万人迷
- 天龙人们强取豪夺的万人迷章节目录,提供天龙人们强取豪夺的万人迷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332289字07-27
- 快穿:恶毒女配抢走了金手指
- 快穿:恶毒女配抢走了金手指章节目录,提供快穿:恶毒女配抢走了金手指的最新更新章...
- 2309898字07-27
- 奶爸奶自己有什么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流浪小新)的经典小说:《奶爸奶自己有什么错》最新章节全文...
- 2537405字07-25
- 傻白甜美人重生后杀疯了
- 1104524字04-23
- 穿成豪门亲妈我哈哈哈哈哈哈
- 1383962字05-23
- 全能歌姬辅助系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锦依卫69)的经典小说:《全能歌姬辅助系统》最新章节全文阅...
- 5630406字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