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 钢与柔:成都东郊的双重叙事
向远处,映着路灯的光,像串流动的珍珠。孩子们则在篮球架下追逐,惊起了趴在晾衣绳上的蜻蜓。烟囱在夜色里成了沉默的剪影,顶端的航标灯一闪一闪,倒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
九八年夏天,红光厂开始减产,烟囱冒烟的时间越来越短。有天夜里,我被父亲的叹息声惊醒,看见他站在窗前,望着漆黑的烟囱发呆。月光洒在他的背影上,竟比车间的机床还要沉默。后来烟囱彻底不冒烟了,拆的时候,好多老工人都来送行,有人摸着砖缝哭了,说那砖上还留着他们年轻时的手印——当年砌烟囱时,每人都在砖上摁了个手印,说要跟烟囱一起"为人民服务"。
如今烟囱的位置成了东郊记忆的观景台,保留了半截红砖烟囱作为装饰,上面爬满了绿植,倒像是给老烟囱戴了顶绿帽子。有次我带着父亲去逛,他站在烟囱下,指着砖缝里嵌着的小石子说:"这是当年砌烟囱时,我跟你王伯伯偷偷塞进去的,说等老了就来看看谁的石子还在。"话音刚落,一群年轻人举着相机跑过来,对着烟囱拍照,镜头里,父亲的白发和红砖烟囱叠在一起,像幅新旧交织的画。
四、厂边的江湖
建设路的贸易公司是东郊的"奢侈品店"。玻璃柜台里摆着上海产的雪花膏,青岛的花布,还有凭票才能买的自行车。厂里发的布票,母亲总舍不得用,攒到过年才带我去扯块红布,做件新棉袄。售货员阿姨认得厂里的人,看见父亲的工装就笑着说:"红光厂的?今天有紧俏的肥皂,给你留了两块。"
澡堂隔壁的理发店是个热闹去处。王师傅的推子比车间的机床还快,"咔咔"几下就剪好一个"工人头"。他总爱跟顾客打听厂里的事,剪着剪着就说:"听说你们车间要涨工资了?"要是遇见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他还会多剪两剪刀,说:"给英雄剪得精神点!"镜子旁边挂着张老照片,是他年轻时给苏联专家理发的样子,那时他还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邮局的李大姐对106信箱的信件门儿清。每天上午十点,她都会把盖着"成都106"邮戳的信分好,用红绳捆成捆,等着厂里的通讯员来取。有次我替父亲寄信,她看了地址就说:"3分箱是检验科的吧?张科长的信昨天刚寄走。"她的抽屉里总放着块橡皮,专门用来修改写错信箱号的地址,橡皮上的字都被磨平了,却比任何公章都让人信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供销社的柜台前总排着长队。凭厂里发的购货本才能买到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13页
相关小说
- 恶毒反派太惹火,狂情霸少狠狠爱
- 恶毒反派太惹火,狂情霸少狠狠爱章节目录,提供恶毒反派太惹火,狂情霸少狠狠爱的最新...
- 746663字07-26
- 救命!快把女主带走[快穿]
- 救命!快把女主带走[快穿]章节目录,提供救命!快把女主带走[快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115713字07-26
- 快穿:绝美宿主在线撩病娇主神
- 快穿:绝美宿主在线撩病娇主神章节目录,提供快穿:绝美宿主在线撩病娇主神的最新更...
- 522833字07-25
- 和未来反派协议结婚后[穿书]
- 和未来反派协议结婚后[穿书]章节目录,提供和未来反派协议结婚后[穿书]的最新更新章...
- 677725字07-25
- 穿成丧尸异世的Omega
- 穿成丧尸异世的Omega章节目录,提供穿成丧尸异世的Omega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425847字07-26
- 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
- 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章节目录,提供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096177字0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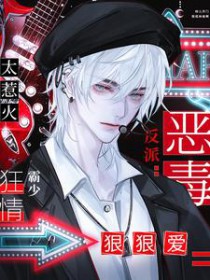
![救命!快把女主带走[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5/65958/65958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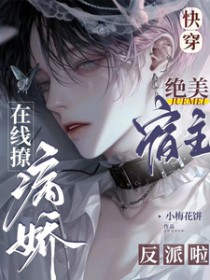
![和未来反派协议结婚后[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5/65291/65291s.jpg)

![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5/65712/65712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