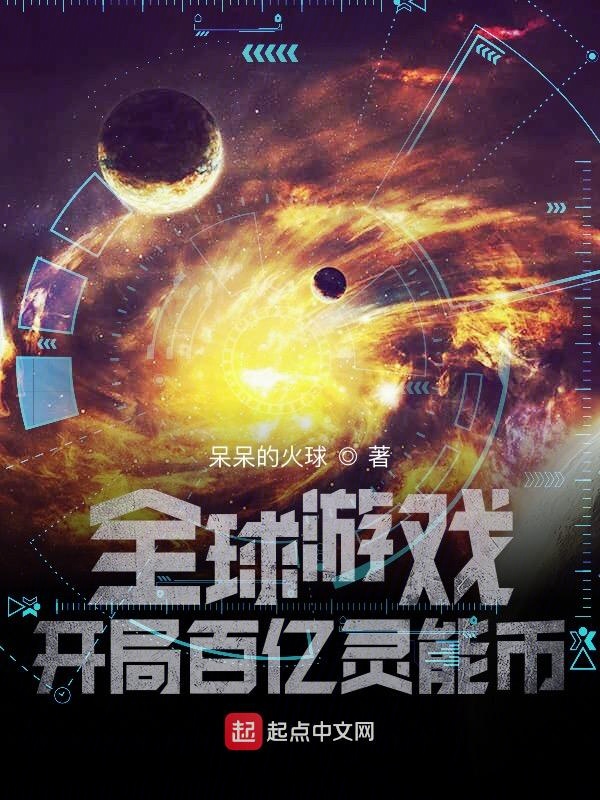第2419章 传承的温度
图书馆的落地窗映着秋日暖阳,林砚之将那支钢笔轻轻放在展柜里。玻璃下方的铭牌写着“1987年刑侦人员林建国使用过的钢笔”,旁边并排放着的,是母亲的蓝布衫、老陈的拐杖,以及赵峰修复的那半枚警徽。这是希望小学新建的校史博物馆,三十七年来的故事,都被妥帖地收在这里。
“林老师,孩子们在等您讲‘钢笔的故事’呢。”志愿者小张跑进来,她是这所学校的第三十届学生,现在是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她手里捧着束向日葵,花瓣上还沾着露水,“这是云南的陈校长托人捎来的,说让您放在展柜前。”
林砚之将花插进玻璃瓶,阳光透过花瓣,在展柜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她走到教室时,三十多个孩子正坐得笔直,小脸上满是期待。黑板上画着时间轴,从1987年的雨夜一直延伸到2025年的校庆,每个节点旁都贴着照片,像串被时光串联的珍珠。
“这支钢笔救过三个人的命。”林砚之拿起复刻的钢笔模型,“1987年的夏天,它的主人用它记录下证据,保护了赈灾款;1988年,它帮迷路的孩子写下家庭地址;2003年,它在火灾现场留下了求救信号......”
孩子们的眼睛亮闪闪的。最前排的小男孩举起手:“林老师,英雄是不是都会魔法呀?”
教室里爆发出笑声。林砚之蹲下身,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英雄的魔法,其实是坚持。就像老槐树,一年年扎根,才能挡住风雨。”她指向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叶已经蔓延到教学楼顶,树洞里的铁皮盒被移到了博物馆,里面的证据成了最珍贵的展品。
放学后,林砚之在办公室整理信件。来自云南的信封上贴着向日葵邮票,母亲的字迹依然清秀:“之之,云南的小学也建了博物馆,孩子们说要把你的故事加进去。张岚寄来的法律手册很有用,上周刚帮村寨调解了宅基地纠纷。”信末画着个小小的笑脸,旁边写着“赵老师在教孩子们修课桌,说要给希望小学捐批新桌椅”。
桌角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老陈的护工打来的。老人上周突发心梗住院,现在刚醒过来,非要见她不可。林砚之赶到医院时,老陈正举着放大镜看希望小学的校庆相册,指腹在父亲的照片上轻轻摩挲。
“这张拍得好。”老陈的声音还有些虚弱,“你父亲当年总说,破案不是为了勋章,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睡安稳觉。”他从枕头下摸出个红布包,“这是他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
褪色的党员证上,“林建国”三个字刚劲有力,入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全球游戏:开局百亿灵能币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呆呆的火球)的经典小说:《全球游戏:开局百亿灵能币》最新...
- 4162247字06-29
- 网游:开局抽奖隐藏职业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笔下有愚)的经典小说:《网游:开局抽奖隐藏职业》最新章节...
- 1638744字07-30
- 重生之一生一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末日行)的经典小说:《重生之一生一世》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429307字06-26
- 快穿之咸鱼她躺赢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林喵喵)的经典小说:《快穿之咸鱼她躺赢了》最新章节全文阅...
- 3977058字07-30
- 中国篮球复兴之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中儒先生)的经典小说:《中国篮球复兴之路》最新章节全文阅...
- 487573字10-23
- 成为领主后,觉醒了进化天赋
- 成为领主后,觉醒了进化天赋是由作者光闪著,免费提供成为领主后,觉醒了进化天赋最新...
- 2047971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