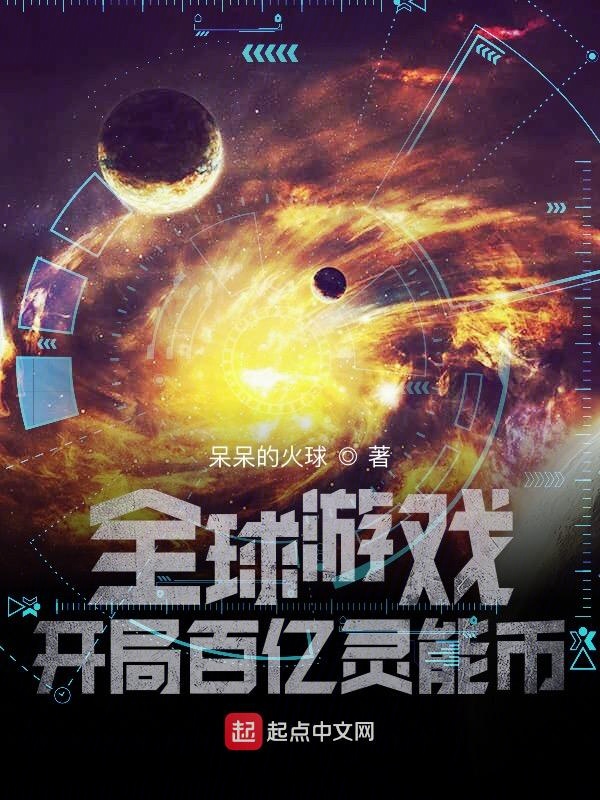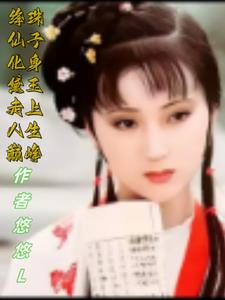第2418章 时光里的接力
校庆后的第三个周末,林砚之接到了张岚的电话。纪检委办公室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上投下条纹阴影,张岚正用红笔在1987年的案件卷宗上圈画,桌角的相框里,戴红领巾的小女孩举着奖状,钢笔在胸前闪着光。
“这是当年所有涉案人员的最终处理报告。”张岚推过来一叠文件,“赵副局长的残余势力上周已全部落网,瑞士银行的账户也通过国际司法协助完成了解冻。”她指向其中一页,“有意思的是,这些钱除了建校,还匿名资助了三十七名贫困生,其中有十二人现在成了公益律师。”
林砚之的目光落在“受助者名单”上。赵峰的名字赫然在列,资助年限从1988年到1995年,落款处的汇款账号,与老陈当年的工资卡完全一致。她忽然想起希望小学的铁皮盒,某张毕业照背面写着“学费已代交,安心读书”,笔迹正是父亲的。
“您见过陈校长吗?”林砚之轻声问。
张岚的笔顿了顿,指尖划过照片里母亲的身影:“她总说我像她失散的女儿,每年都给我寄文具。”她从抽屉里取出个褪色的布包,“这是她临走前给我的,说等我真正理解‘正义’二字时再打开。”
布包里是本刑侦笔记,扉页写着“给之之”。翻开的瞬间,林砚之的呼吸停滞了——里面贴着父亲的照片,每张下面都有母亲的批注:“1986年冬,他冒雪送迷路老人回家”“1987年春,帮小贩追回被抢的货款”。最后一页夹着张孕检单,日期是1987年7月,恰好是父亲“牺牲”前一个月。
“原来她早就知道我的存在。”林砚之的眼眶发热。那些年母亲的“缺席”,或许不是抛弃,而是用最笨拙的方式保护她远离危险。
窗外传来鸣笛声,是检察院的车。张岚起身整理卷宗:“我们要去云南一趟,给那位女老师做正式笔录。”她忽然笑了,“她说想把当年的故事写成教材,让孩子们知道,英雄未必都穿着铠甲。”
云南的山路蜿蜒曲折,林砚之坐在颠簸的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梯田。女老师所在的村寨小学藏在云雾里,木质教学楼的墙上画着彩虹,孩子们的笑声穿透晨雾,与希望小学的铃声重叠在一起。
“这是林警官当年设计的课表。”女老师指着墙上的泛黄纸张,“他说山区孩子要学知识,更要学怎么保护自己。”她掀开讲台上的木箱,里面是几十本手抄的法律手册,每本的扉页都画着小小的警徽,“这些是赵老师每年寄来的,他说总有一天用得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2页
相关小说
- 铠甲勇士之倒追非人类警官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安之如菲)的经典小说:《铠甲勇士之倒追非人类警官》最新章...
- 1058319字07-30
- 末世,我的空间能种出世界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X的狂想日记)的经典小说:《末世,我的空间能种出世界树》最...
- 721348字07-30
- 全球游戏:开局百亿灵能币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呆呆的火球)的经典小说:《全球游戏:开局百亿灵能币》最新...
- 4162247字06-29
- 绛珠仙子化身黛玉,走上人生巅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悠悠L)的经典小说:《绛珠仙子化身黛玉,走上人生巅峰》最新...
- 1316917字07-30
- 基建末世:穿得越粉,杀人越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巫秋尔)的经典小说:《基建末世:穿得越粉,杀人越狠》最新章...
- 1068257字07-30
- 原神:在枫丹廷开一家糕点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帝寒轩)的经典小说:《原神:在枫丹廷开一家糕点铺》最新章...
- 909132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