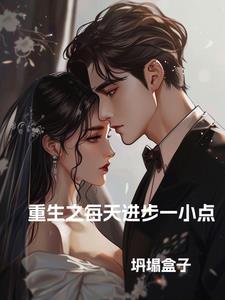后记(亲情友情向)
。澈儿见了笑道:“它倒比朕金贵。” 小内侍答:“它会说陛下的话呀,冻着了谁来提醒‘民心安’呢?” 雪落在紫藤花架上,压得枝桠轻颤。鹦鹉忽然对着南城的方向喊:“下雪了,百姓的柴够吗?” 澈儿望着远处贫民窟的屋顶,对禄公公说:“传旨,给南城添发冬柴,要干透的松柏枝,好烧。”
后记十六:旧笺染泪,友声藏念
澈儿的紫檀书箱底层,压着个北地松木盒。里面装着萧珩寄来的信笺,多是在战事间隙写的,字迹潦草,偶有墨团,还沾着风沙的痕迹。最底下那张最破,边角都磨卷了,上面只写着:“陛下,今日见雁南飞,忽然想起国子监的纸鸢,也是往南飞的。”
那是萧珩刚到北境的冬天。他带军打了场硬仗,信是在伤兵营写的,墨迹里混着暗红——后来才知,是他臂上的血没擦净,蹭到了纸上。澈儿收到时,对着那张纸看了半夜。想写“保重”,嫌太轻;想写“盼归”,怕他分心。最后只画了只展翅的雁,旁边题了行小字:“待君归,共放风筝。”
后来萧珩凯旋,两人真的去了国子监旧址。春日的风很暖,纸鸢飞起来时,萧珩忽然说:“其实那天我怕再也回不来,才写那封信的。” 澈儿握着线轴的手紧了紧,抬头见纸鸢越飞越高,几乎钻进云里,笑道:“你看,它这不就飞回来了?” 风把线扯得笔直,像根看不见的绳,一头系着皇城的朱墙,一头系着北境的烽烟,系着两个少年人从未说出口的牵挂。
如今那些信笺被澈儿用蓝锦缎包着,放在萧珩送的木盒里。松木的香气混着淡淡的墨味,像极了那年国子监的午后——萧珩趴在石桌上写信,他在旁磨墨,砚台里的墨香混着窗外的槐花香,也是这样清透。偶尔翻开,仿佛还能听见雁鸣掠过信纸,带着北境的风,和一句没写完的“我想你了”。
后记十七:石案拓碑,文脉藏根
殷照临曾带澈儿去孔庙拓碑。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少年的他蹲在“万世师表”的碑前,手里攥着生宣和墨包,笨手笨脚地捶打。墨汁溅得满手都是,连鼻尖都沾了点黑,像只花脸猫。
“拓碑要轻要匀,”殷师蹲在他身边,手里的墨包在宣纸上慢慢擦过,动作像抚摸什么珍宝,“就像读书,急不得,得一字一句啃透。” 他拓坏了三张纸,才勉强成了一幅。拓片上的“师”字缺了个角,是早年战乱时被流矢崩的。殷师拿起看了看,用朱笔在缺口处补了一笔:“字有缺,人也有缺,能补就不算遗憾。”
后来那幅拓片被澈儿裱起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公子下班了)的经典小说:《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452867字05-05
- 追燕
- 505604字09-10
- 我是晋上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坍塌盒子)的经典小说:《我是晋上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708807字11-17
- 心机女上位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爱吃柚子1995)的经典小说:《心机女上位史》最新章节全文...
- 2003377字11-06
- 华娱似水流年
- 5312950字03-13
- 敢爬墙就操死(1v2)
- 566193字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