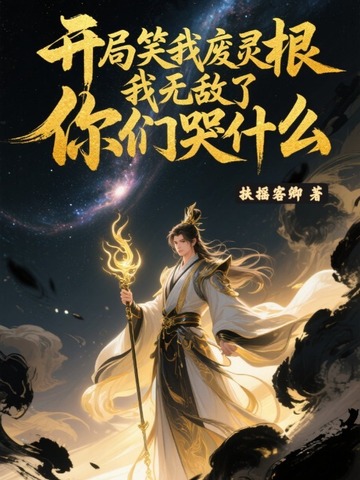第363章 河口冲积扇与咸淡水粮种
船帆带着泥炭沼泽的寒气继续前行,甲板上的陶瓮队列已按 “气候带” 整齐排列 —— 最东侧的 “寒带区” 并排放着野慈姑与野荞麦的容器,罐口的白霜与西侧 “热带区” 耐盐禾罐壁的盐晶形成鲜明对比。宝儿用细棉线将各区域的代表种子串联起来,从深褐色的沙棘豆到白色的野慈姑球茎,丝线在阳光下形成七彩的光带,恰似将沿途的气候密码编织成链,线头系在船舵的铜环上,随航向轻轻摆动。
“夫人,水色在变!” 哈桑举着舀水的木瓢大喊,瓢中原本青黑的泥炭水正渐变为浑浊的土黄,与冲积平原的河水泥色相近却更显厚重,“这水一半咸一半淡,舌头能尝出两重味,测深绳的铅锤上缠着半咸水的水草!” 他说得没错,船舷边的水面漂浮着奇特的植物,根部浸在咸水中呈深褐,叶片露在淡水里显翠绿,如同在同一植株上劈开了两个季节,船桨划动时,能看到咸淡水交汇形成的 “水线” 在桨叶上快速移动,如同双色绸缎在流动。
老舵手用手指捻起船板上的泥沙,沙粒中混着细碎的贝壳:“是河口冲积扇!” 他粗糙的手掌在海图上划出一道弧形,“这种地方是大河入海口的‘拐弯处’,淡水冲的泥沙和海水推的贝壳混在一起,涨潮时泡海水,退潮时喝河水,能长东西的都是两边讨好的机灵鬼,根须得会分哪口是咸水哪口是淡水。” 他的话很快得到印证,了望手在桅杆上大喊,声音里带着久违的兴奋:“东北方向有灰褐色的土塬!像铺在海边的大席子!”
众人望去,只见海岸线处横亘着一片广阔的扇形平原,土色从岸边的金黄渐变为近海的灰黑,如同被大地铺开的调色盘。平原上交错分布着淡水河渠与咸水洼塘,河渠里的水清澈见底,游动着银色的小鱼;洼塘里的水泛着盐花,栖息着青色的蟹类,两者的分界处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叶片正面深绿如墨,背面灰白似霜,风过时翻转如浪,仿佛在演示着对两种水质的适应。
正午的阳光将平原晒得温热,温度计显示气温较泥炭沼泽升高八度,却比沙质海岸低五度,形成独特的 “过渡温区”。空气里弥漫着咸淡水混合的气息,吸入肺中既有河泥的腥甜,又有海水的咸涩,让船员们想起泉州港的味道 —— 那里的水也带着这种 “两不像” 的气息,只是更淡些。更奇特的是,平原上的植被会随潮汐变化:涨潮时,咸水洼塘的植物会舒展叶片;退潮后,淡水河渠的植物则加速生长,仿佛在遵循某种古老的生物钟。
“看那些河渠与洼塘的交界!” 曾在闽江口种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斗罗之我是宁荣荣的守护灵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奋斗中的小文)的经典小说:《斗罗之我是宁荣荣的守护灵》最...
- 605303字07-23
- 麒麟武神
- 1446446字07-24
- 开局笑我废灵根,我无敌了你们哭什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扶摇客卿)的经典小说:《开局笑我废灵根,我无敌了你们哭什么...
- 346514字07-24
- 《公爵小姐是个吸血鬼,但她只吃番茄》
- 120532字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