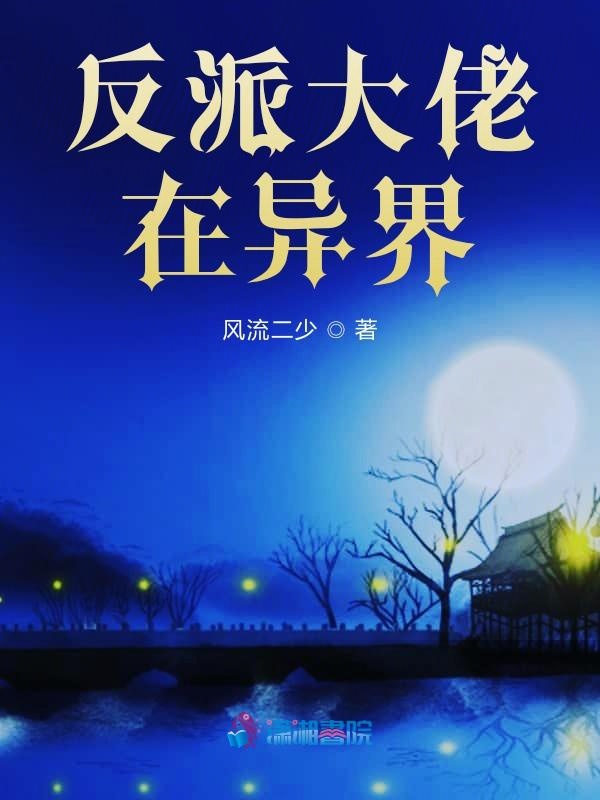第373章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怨恨,都穿透厚厚的墙壁,撞击着他的耳膜。
他面上平静无波,心中却非毫无涟漪。
一丝沉重掠过。
试问,他所做的这一切,需要依靠穿越者的“先知先觉”吗?
他阻止那些充斥“是矣”的垃圾卷子取中,难道不是任何一个读过圣贤书、尚存一丝良知和气节的官员本就该做的事情吗?
他坚持取中真才实学,难道不是孔孟反复强调的“选贤与能”、“有教无类”吗?
难道只有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吗?
那些对错,那些“圣人之道”,古人比他烂熟于心千倍万倍!
严嵩初入翰林时,不也曾是那个满怀经纶、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
他也曾意气风发,针砭时弊,笔下文章也曾激扬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
那时的他,心中难道没有正义?
徐阶被夏言赏识提拔之初,锐气风发,敢于谏言,也曾因不满权阉被罢黜回乡。
那时,他们心中又何尝没有一杆标尺,知晓何为黑,何为白?
一句“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看似悲悯,实则简化甚至美化了这残酷的过程。
严嵩也好,徐阶也罢,他们并非一夜之间变成了自己曾经憎恶的模样。
那是一个缓慢的、几乎难以察觉的侵蚀过程。
严嵩最终变成那棵蔽日遮天、结满贪腐毒瘤的“青词宰相”,不是因为他遗忘了圣人的道理,而是当他在权力场中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感受到冰冷现实的挤压后,他“悟了”。
他悟透了生存之道——唯有逢迎上意,揣摩帝心,结成党羽,才能手握重权,爬得更高,活得更久,荫蔽子孙。
那个心中尚存正义的少年严嵩,在那个残酷的领悟过程中,早已经被这巨大的洪流碾碎、吞噬、重构了。
活下来的,是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套生存法则的严嵩。
同样的蜕变,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速度和程度上演着,严嵩,徐阶……乃至史书中无数或大或小的名字。
大明走到今日这般田地,积弊丛生,沉疴难起,难道是哪一个独夫贼子或偶然因素造成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是大明这架庞大而腐朽的机器。
是那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是那“不逢迎上意便寸步难行”的官场铁律。
是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责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