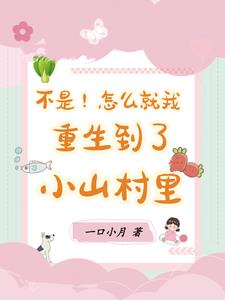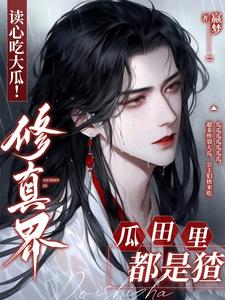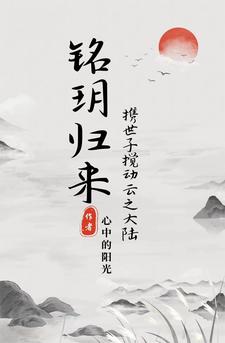第346集:《罕见病治疗突破》
中的坐骨神经分布惊人地吻合。“这不是巧合。”他在患者交流群里写道,“也许古老的智慧早就发现了我们没看见的规律。”
第三章:银针下的转机
试验进行到第 9 个月,转折点悄然而至。
艾莎在一次治疗后,突然想试试拿起小提琴。她颤抖着把琴弓搭在弦上,当《爱的礼赞》的旋律断断续续响起时,守在一旁的母亲捂住了嘴,泪水从指缝里涌出来——这是她生病后第一次完整拉出乐句。
更令人振奋的是数据。林砚团队每周更新的试验日志显示,实验组的复发率开始明显低于对照组。有位原本每月发作一次的患者,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出现症状;还有几位患者的 MRI 影像显示,新增的“亮斑”数量显着减少。
霍夫曼教授起初对这些数据嗤之以鼻,认为是“安慰剂效应”。直到他亲眼看到一位患者的对比影像:治疗前,大脑白质区的病灶像星星一样密集;治疗半年后,大部分病灶的信号强度减弱,如同被乌云遮蔽的星光。
“这不可能。”他反复核对数据,甚至亲自监督了几次针灸治疗,看着陈默精准地刺入那些他从未关注过的“穴位”。当他发现这些穴位大多位于神经节密集区时,不得不承认:“也许这些点真的是神经修复的关键节点。”
团队内部的突破同样令人惊喜。杨伯根据患者的反馈,调整了草药配方——欧洲人的体质偏“燥热”,他减少了温补药材的用量,加入具有“清凉”特性的当地草药“洋甘菊”,患者的耐受性显着提高。
“苗医讲究‘一方一境’,在贵州用的方子,到了欧洲就得变。”杨伯在视频会诊时对林砚说,“就像山里的竹子,到了平原要换种法,才能长得直。”
这种“在地化”调整,让疗法的有效率又提升了 12%。当试验进行到第 15 个月时,初步统计结果出来了:实验组的复发率比对照组降低了 58%,且没有严重不良反应。这个数字让整个团队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原本的预期是降低 30%。
那天晚上,科隆的夜空飘着细雨。林砚和团队成员在医院附近的小酒馆庆祝,酒杯里的啤酒泛起细密的泡沫。陈默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饰风铃,轻轻一晃,清脆的响声在雨声中格外清晰。“这是我奶奶给的,说能驱散晦气。”他笑着说,眼角却闪着光,“现在看来,它真的带来了好运。”
第四章:柳叶刀上的回响
整理试验数据的日子,林砚团队几乎住在了实验室。他们要将苗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口小月)的经典小说:《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1162626字07-30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读心吃大瓜!修真界瓜田里都是猹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嬴梦)的经典小说:《读心吃大瓜!修真界瓜田里都是猹》最新...
- 1498593字11-19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铭玥归来携世子搅动云之大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心中的阳光)的经典小说:《铭玥归来携世子搅动云之大陆》最...
- 1379840字12-01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