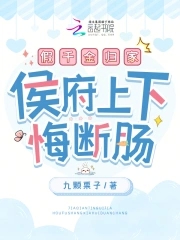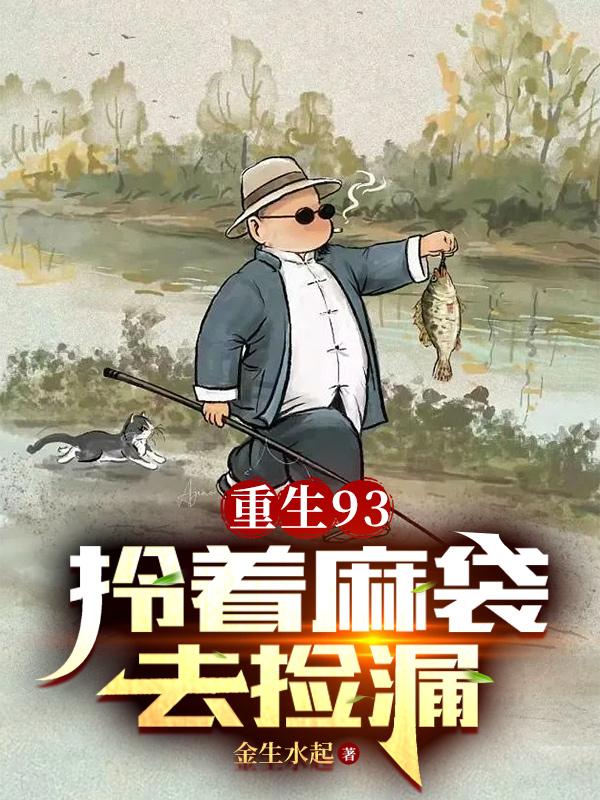第382章 冈仁波齐:神山不语,众生默行
车轮在碎石与浮尘中沉重前行,远处的雪峰愈发清晰。那是冈仁波齐,西藏阿里地区的圣山,被藏传佛教、印度教、苯教与耆那教共同尊崇为“世界中心”,一座无需语言也能震撼心灵的高原巅峰。
地图上不过一小点,在现实中却如天界之柱,笔直而孤傲地立于万山之中。
此刻,我坐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扎达路口,手中翻阅着《地球交响曲》,笔下尚未落定的章节仿佛在呼吸,与我心脏的跳动同步。我深吸一口薄氧空气,仿佛在为即将开始的“转山”仪式做准备。因为我知道——冈仁波齐不只是风景,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人的心。
塔钦,是进入冈仁波齐的门户小镇,也被称为“神山脚下的等待之地”。在这里,我遇到各种肤色与装束的朝圣者:来自拉萨的老喇嘛、来自印度的苦行僧、来自成都的骑行者,还有一位操着藏腔普通话的小男孩,骑着一辆生锈的单车,从村口笑着向我挥手。
他喊我:“叔叔,要去神山吗?”我笑着点头,他便头也不回地往山那边骑去,像是早已知道答案。
在客栈老板的建议下,我放下车辆与行囊,轻装出发,只带着干粮、水、御寒衣物和《地球交响曲》的笔记本。
我要开始的是——冈仁波齐转山,一个耗时两至三日、全程五十二公里、翻越海拔超五千六百米卓玛拉山口的艰难朝圣之路。
天色微亮,我跟随一群藏族人一起起步。他们中有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叩首;有少年肩背念珠,沉默前行。每一个人都像一粒尘埃,向神山缓慢靠近,却又毫不退缩。
不久,我便看到了觉巴寺——这座位于冈仁波齐南面山脚的小寺,只有几个僧人守护,却仿佛被时间遗忘。寺庙里一口铜钟随风低鸣,像是在回应山的沉默。
寺里的年长喇嘛望着我,语气温和:“转山不是祈愿,是交还。”
我问:“交还什么?”
他说:“你以为你在追寻什么,其实是在归还过去的自己。”
那天夜里,我在帐篷中翻阅自己过去在《地球交响曲》上写下的章节,从湖南衡阳到吐鲁番,从北京长城到西藏阿里,我惊觉自己一路上确实在剥离,而非积累。
我在书中写下:“神山的意义,不在于站在它面前,而在于我们愿意放下什么来靠近它。”
第二日清晨,天降细雪,风速骤然加剧。我们攀升至五千六百米的卓玛拉山口。这里是整个转山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是许多朝圣者中止脚步的地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勇者可以不活,但不能没活
- 1609267字07-29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颗栗子)的经典小说:《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最新章...
- 332519字07-29
- 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金生水起)的经典小说:《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最新章节...
- 8159885字07-24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