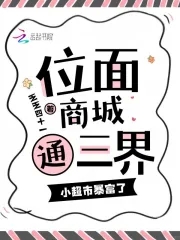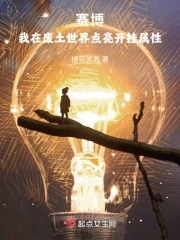《东坡仙粥:黄芪春韵》上卷
,黄芪本是补元珍
上元节刚过,惠州的梅花还剩最后几瓣残红。苏轼收到好友钱勰从杭州寄来的信,信中说:“闻子由言兄患消渴,弟忆昔年在徐州,见一老叟以黄芪粥疗此症,百试不爽。其法:取黄芪五钱,煮水取汁,入粳米煮粥,空腹食之,如春日培土,能生万物之气。”
信末还附了一段《神农本草经》的抄录:“黄芪,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苏轼反复摩挲着信纸,想起元丰年间在黄州,曾见农人将黄芪根晒透了藏起来,说是“冬藏春用,能抵半副人参”。他对朝云道:“钱兄素来严谨,他推荐的法子,定有道理。”
可岭南的药铺里,黄芪多是本地所产的“南黄芪”,根细味淡。苏轼便托人往北方采买“北黄芪”——据说山西产的绵黄芪最佳,根如箭杆,断面呈金井玉栏,得太阴之精,补肺气而固表,升脾气而利水。等待药材的日子里,他试着用南黄芪煮粥,虽也有些回甘,却总觉力道不足,夜里仍渴醒数次。
一日午后,他在草庐前晒太阳,见一只老母鸡带着雏鸡啄食墙边的黄芪嫩叶,雏鸡吃得欢实,绒毛油光水滑。他忽然悟到:“草木有灵,需得顺应时节。黄芪春生苗,夏长叶,秋收根,冬藏精,我此刻用其叶,正如取未熟之果,自然效力不足。”便让仆役在院中辟出一块地,埋下南黄芪的种子:“且等来年,看它能否生根发芽,得此地之气。”
半月后,北黄芪终于送到。苏轼拆开油纸包,一股醇厚的药香扑面而来,如陈年的米酒,混着阳光的味道。他拿起一根细看,根须完整,皮黄肉白,断面的纹路如年轮般清晰。朝云笑道:“先生见了这药,眼里都有光了。”苏轼哈哈一笑:“这哪里是药?这是催我活下去的春信啊!”
第三回 初试粥香消燥渴,一瓯能抵万黄金
惊蛰那日,雷声隐隐,惠州的泥土里钻出新绿。苏轼按照钱勰的法子,亲自煮起黄芪粥。他先将黄芪用清水泡了半个时辰,待根须舒展,便放入砂锅中,加井水三升,大火煮沸后,改小火慢煎。药香渐渐弥漫开来,初时如远山含黛,带着一丝清苦;煎到一个时辰,苦尽甘来,竟有蜜般的甜香从锅盖缝里钻出来。
朝云在旁研墨,笑道:“先生煮药,倒比写词还认真。”苏轼头也不抬:“药如文,需字字斟酌。火大了则焦,火小了则力不足;时短则味浅,时长则味浊。”他守在炉边,不时用竹筷搅动锅底,见黄芪水渐渐变成琥珀色,便滤出药汁,再将淘洗干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无敌了
- 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无敌了是由作者威廉陛下著,免费提供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
- 2587722字11-01
- 位面商城通三界,小超市暴富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乏乏四十一)的经典小说:《位面商城通三界,小超市暴富了》最...
- 430219字11-30
- 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库
- 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库是由作者王国泪痕著,免费提供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
- 2137255字07-27
- 海平线的末日挣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心直口快的林锦)的经典小说:《海平线的末日挣扎》最新章节...
- 3740441字07-25
- 赛博:我在废土世界点亮开挂属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桃花苏苏)的经典小说:《赛博:我在废土世界点亮开挂属性》...
- 561300字03-06
- 我在末世苟成大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盛夏的东风)的经典小说:《我在末世苟成大佬》最新章节全文...
- 1005882字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