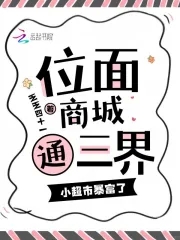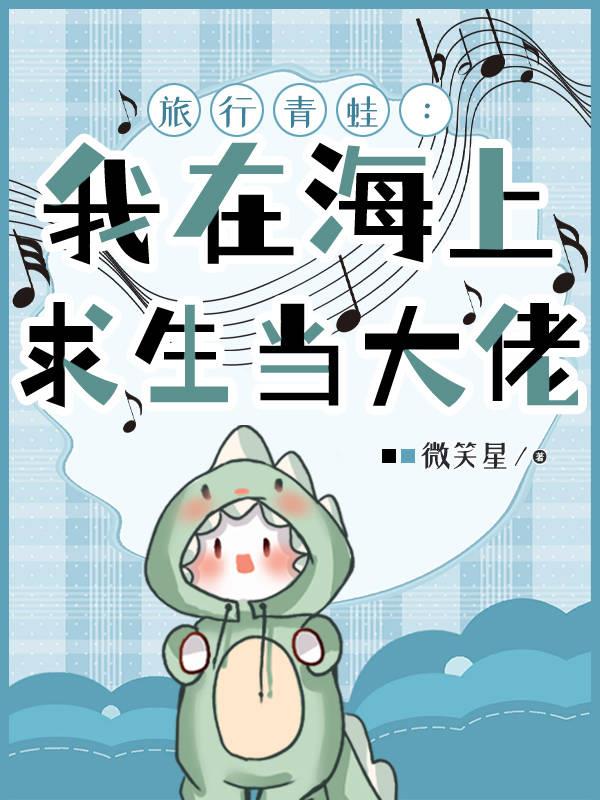《东坡仙粥:黄芪春韵》上卷
《东坡仙粥:黄芪春韵》
楔子
绍圣四年的岭南,腊月的风带着海腥气,刮过惠州的东坡草庐。苏轼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棉袍,坐在竹榻上,望着案头那碗冷透的汤药,喉间泛起一阵燥渴。自去年被贬至此,消渴之症便如影随形——白日里饮尽一缸水仍觉喉咙冒烟,夜里尿意频频,刚合上眼就得起身,折腾得形容枯槁。
这夜,他恍惚梦见自己回到了眉山老宅,院角那株百年黄芪正抽出新芽,嫩黄的芽尖顶着晨露,顺着根须往土里钻,竟钻出一股清冽的甘泉。他俯身去饮,水入喉间,如春风拂过枯田,浑身的燥热瞬间消了大半。惊醒时,窗外的月光正落在窗台上那株友人送的盆栽黄芪上,叶片上的绒毛沾着夜露,在月下闪着细碎的光。他摸了摸干渴的嘴唇,忽然想起梦中那股甘润,心头一动。
上卷:渴饮南海浪,药香入梦来
第一回 瘴疠侵体生消渴,坡仙病骨叹伶仃
惠州的冬日常有回南天,墙壁渗着水珠,空气黏得像化不开的糖稀。苏轼放下手中的《周易》,又灌下一大碗凉茶,可舌尖的灼痛感丝毫未减。他苦笑一声,对侍妾朝云道:“你看我这病,倒比岭南的荔枝还顽固。”朝云眼圈泛红:“先生前日还能写词,昨日起连握笔都觉手颤,这可如何是好?”
当地的老郎中来看过,诊脉后摇头:“大人脉象洪数,舌红少津,是消渴重症。岭南多湿热,大人本就年高,又兼忧思过度,肾阴亏耗,胃火炽盛,如釜中无水,岂能不燥?”开的方子用了知母、黄柏,服下后虽稍有缓解,却总反复。苏轼望着窗外那株被台风刮断枝桠的榕树,叹道:“我这身子,倒不如这榕树坚韧。”
一日,他在东江畔散步,见渔夫们赤足在滩涂劳作,虽日晒雨淋,却少有消渴之症。便上前请教,老渔夫笑道:“我们靠水吃水,渴了就喝江水,饿了就煮些杂粮粥,里头常放些‘土黄芪’——就是山坡上那种开小紫花的根,吃着踏实。”苏轼记下“土黄芪”三个字,见江面上水汽氤氲,忽然想起《黄帝内经》里“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的话,若脾胃能化水谷为精气,或许能解这燥渴?
夜里,他又梦到那株黄芪。这次,黄芪的根须在土里蜿蜒,竟与江河的支流重合,根须吸收的水分,顺着茎秆往上走,在叶片上凝结成露,滴落在他掌心,凉丝丝的,带着泥土的腥甜。他惊醒时,朝云正端来温水,他喃喃道:“黄芪…或许真能救我。”
第二回 故人千里传药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无敌了
- 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无敌了是由作者威廉陛下著,免费提供重生末世:我的女神军团...
- 2587722字11-01
- 位面商城通三界,小超市暴富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乏乏四十一)的经典小说:《位面商城通三界,小超市暴富了》最...
- 430219字11-30
- 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库
- 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库是由作者王国泪痕著,免费提供nba数据自由定制,谗哭科詹...
- 2137255字07-27
- 龙珠开局,寻爱超神,漫游诸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杰克林斯图亚特)的经典小说:《龙珠开局,寻爱超神,漫游诸天...
- 3400663字11-15
- 全民神只重生后5S天赋我超神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是个豆团子)的经典小说:《全民神只重生后5S天赋我超神啦》...
- 752343字10-04
- 旅行青蛙:我在海上求生当大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笑星)的经典小说:《旅行青蛙:我在海上求生当大佬》最新...
- 1520031字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