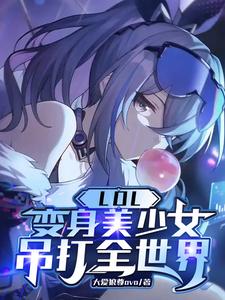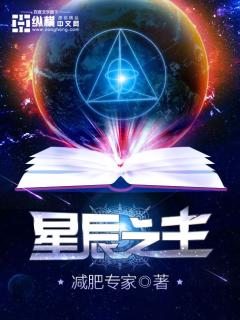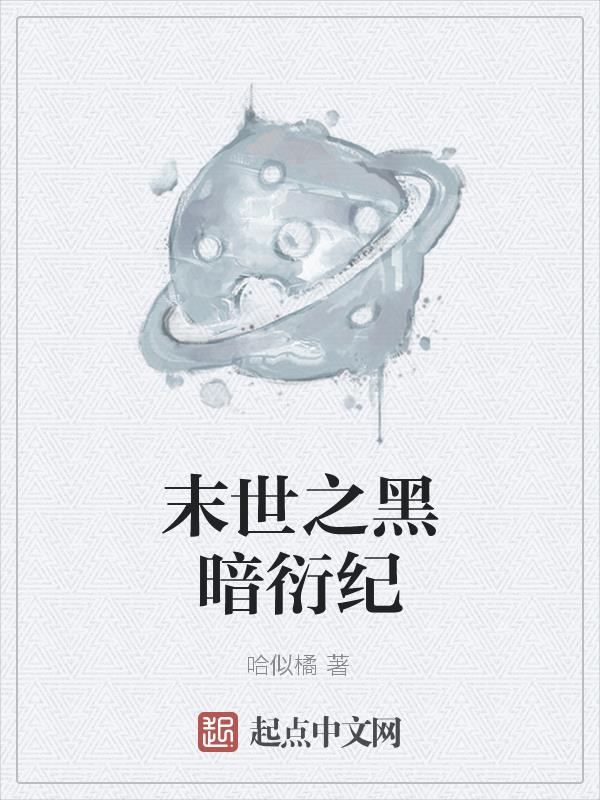云樵遇仙得仙芪 上卷
云樵将籽种小心收好,采了贝母下山。王阿婆喝了贝母汤,咳嗽渐轻,听闻云樵的奇遇,抚着他的手说:"那定是黄芪仙子显灵了!老辈人说,仙子原是恒山的山神侍女,为救瘟疫中的百姓,偷了天庭的药籽撒在背阴坡,自己却被压在悬瓮洞,只每年清明能出来透透气。"
转年开春,云樵按仙子的嘱咐,将籽种播在背阴坡的岩缝里。籽种入土的第三日,竟冒出淡紫的芽,芽尖顶着露珠,在雾中轻轻颤动,像极了仙子轻颤的睫毛。
第二回 春生时节辨阴阳
谷雨过后,背阴坡的黄芪苗蹿得有半尺高,羽状复叶在雾里舒展,叶背的绒毛沾着水汽,像裹了层银纱。云樵每日辰时来浇水,发现个奇事:同是一片坡地,长在青石北侧的苗更壮实,长在南侧的却有些蔫软。
他请教村里的老药农张伯。张伯捻着胡须蹲在坡上,扒开苗根的土块说:"你看这土,青石北的土凉润,青石南的土温燥。黄芪性温,却怕火气过盛,背阴坡本是阴地,青石北更是阴中之阴,正好中和它的温性,这就是阴阳相济的理。"
恰在这时,王阿婆的小孙子得了场大病,高烧退后总出虚汗,风一吹就打喷嚏,小脸白得像纸。张伯看了,让云樵挖两棵最壮的黄芪苗,取根须洗净,配了把防风、白术,说:"黄芪性温,味甘,入脾肺二经,就像灶膛里的余火,能把散了的阳气拢起来。白术像黏土,能把阳气固在脾胃;防风像篱笆,能挡住外头的风邪。这三样配着,就像给身子骨搭了道屏风。"
药熬出来是浅琥珀色,甘中带点清苦。孩子喝了五天,虚汗竟收了,见风也不打喷嚏了。云樵在一旁看得真切,张伯又道:"你看这黄芪苗,根往阴处扎,叶朝亮处伸,它自己就懂阴阳调和。人也一样,光补阳气不行,得有阴液托着,就像这背阴坡的雾,能润着黄芪不焦枯。"
云樵把这话记在心里,从此更用心照看那些长在青石北侧的黄芪。有天夜里下暴雨,他担心苗被冲坏,冒雨上山查看,却见背阴坡的雾气聚成个圈,将黄芪苗护在中间,雨珠落在圈外便四散开来。云樵忽然明白,那黄衣仙子从未走远。
第三回 夏长之际识性味
大暑时节,恒山的雨水格外多。背阴坡的黄芪已长到齐腰高,茎秆紫中带绿,顶端抽出细长的总状花序,金黄的小花一串串垂着,像挂满了微型的金钟。云樵发现,经过几场透雨,黄芪的根须在土里长得更密了,轻轻一拔,能带出好些带着湿泥的须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LOL:变身美少女,吊打全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大爱狼尊ovo)的经典小说:《LOL:变身美少女,吊打全世界》最...
- 628791字07-25
- 星辰之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减肥专家)的经典小说:《星辰之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8819801字07-28
- 虹猫蓝兔七侠后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岬新涂)的经典小说:《虹猫蓝兔七侠后传》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939122字05-12
- 末世之黑暗衍纪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哈似橘)的经典小说:《末世之黑暗衍纪》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808004字09-10
- 模板魔术师女明星都是我的充电宝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榆木lee)的经典小说:《模板魔术师女明星都是我的充电宝》最...
- 3404562字06-24
- 极度深寒:我在末世建基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金墉)的经典小说:《极度深寒:我在末世建基地》最新章节全...
- 1251208字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