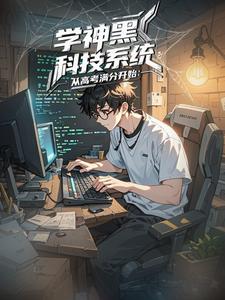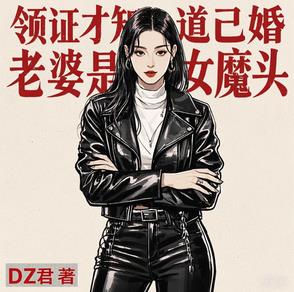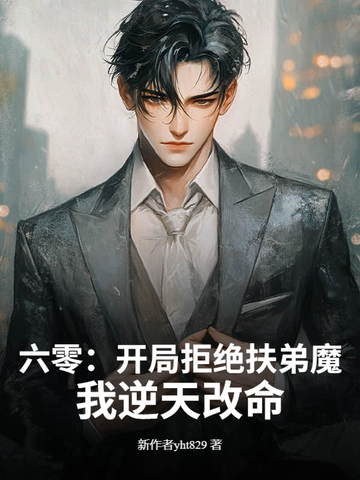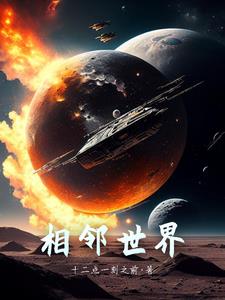第274章 古文字学界大型追星现场
,也挺有趣的,要是看铭文拓片,就脑壳痛了。
那么“申”字有争议,“蔡”字呢?
这玩意又涉及一系列的考证了。
比如容庚就根据魏三体石经“蔡”之古文而做出考释,王国维又说“杀蔡二字同音可相通假”,沈兼士也作了音上的研究。
反正,甲骨文,青铜铭文每一个字的确定都有一系列的考证。
每一字的考释都来自不易。
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
整篇文章,考释的铭文很多。
苏亦的笔记没法面面俱到,只能挑选听得懂的部分来记录。
比如于老考释蔡侯盘上的铭文: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恭)大命,上下陟[衤否],孜敬不惕,肇(佐)天子,用诈(作)大孟姬嫖彝(舟),……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冬(终)岁无疆。”
他的考证,跟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孙百朋几位先生,有异有同。
内容太长,苏亦也没有办法全记,也没有必要,不出意外,明年,古文字的专业学术期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的发表,就把会议的文章都收录其中。
这些古文字学会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到年会,大家就写文章,然后在会议上分享文章,最终评委会挑选出合适文章收录在《古文字研究》上发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整个流程,跟其他学术会议也差不多,奈何,古文字研究太过于枯燥,会议上,不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只能听的份。
那么五十年代挖掘的墓葬,为什么到78年,于老才写考释文章,不会过时了吗?
过时肯定不会过时。
但1978年,蔡侯墓肯定已经不是热点。
于老的文章,也是多年的成功,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场合分享出来罢了。
那么这一年,古文字研究有热点吗?
自然也有。
而且跟考古发掘成果息息相关。
比如其几个月刚刚结束发掘的中山国墓葬。
跟蔡侯墓一样,中山国墓葬,也是因为政府水利工程建设才发现的。
为了配合三汲公社的农田水利建设,从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三汲公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这一调查,发现了公社东南隔河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1页 / 共15页
相关小说
- 学神系统:爆肝高考全科满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Zack00)的经典小说:《学神系统:爆肝高考全科满分》最新章...
- 1206007字07-20
- 开局之我能透支生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七月初三)的经典小说:《开局之我能透支生命》最新章节全文...
- 916791字07-20
- 我,氪命练武,害怕校园不够暴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猫鱼书)的经典小说:《我,氪命练武,害怕校园不够暴力》最新...
- 1199056字07-20
- 领证才知道已婚,老婆是女魔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DZ君)的经典小说:《领证才知道已婚,老婆是女魔头》最新章节...
- 811326字07-20
- 六零:开局拒绝扶弟魔,我逆天改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咕咕饲养员)的经典小说:《六零:开局拒绝扶弟魔,我逆天改命...
- 287069字07-20
- 相邻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十二点一刻之前)的经典小说:《相邻世界》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58178字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