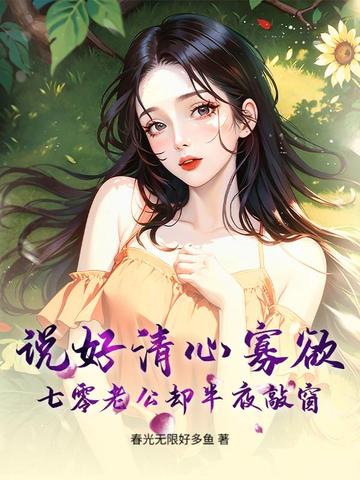第3543章 无法接受
出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滞涩感。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眼角的余光。每一次转身,每一次扫视全场,视线总会不由自主地、极其迅速地掠过那个角落。
宋安始终低着头,专注于手中的笔和笔记本。他几乎没有抬头看黑板,仿佛那些艰深的公式和理论并非通过视觉,而是通过霍桑的声音直接流入他的思维。只有当霍桑抛出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或者某个学生提出一个过于浅显甚至错误的观点时,宋安握笔的手指才会极其短暂地停顿一下,笔尖悬停在纸页上方,似乎在无声地思考或评判。
那短暂的停顿,像投入霍桑心湖的微小石子,激起一圈圈难以言喻的涟漪。
下课铃终于响起,带着解脱般的尖锐。学生们开始收拾书本,交谈声像潮水般涌起。霍桑几乎是立刻低头整理自己的讲稿,动作带着一丝刻意的匆忙。当他再次抬起头,目光再次投向那个角落时——
那里已经空了。
座位上干干净净,仿佛从未有人坐过。只有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冷冽而昂贵的须后水气息,与粉笔灰和年轻汗味格格不入。
霍桑收拾东西的动作停顿了半秒。一种说不清是释然还是更深的烦躁,悄然攥住了他。
第二次,是在霍桑每周一次、限定名额的“意识起源”专题研讨课。地点在他的实验室附属的小型智能会议室。这里更像一个前沿的作战室,环形光带照亮中央的交互式全息沙盘,四周墙壁是巨大的可书写屏幕,上面还残留着上次激烈讨论留下的复杂公式草图和潦草的英文批注。空气里是臭氧、新打印资料油墨和高级清洁剂混合的味道。参与研讨的只有他精选的七名博士生和两名年轻的助理教授,钟书琴也在其中,她坐在靠近霍桑的位置,显得格外专注。
霍桑正在全息沙盘上构建一个极其复杂的多智能体协作模型,模拟原始符号系统的自发形成。模型运行到关键节点,一个关于“共享意图”如何从个体博弈中涌现的分歧点。
“这里,个体A的策略库更新滞后,导致它对群体信号产生误判……”一名助理教授指着沙盘中一个闪烁的红色节点分析道。
“误判本身也可能是系统多样性必需的‘噪音’来源,”霍桑立刻反驳,手指在空气中快速划动,调出底层数据流,“看它的熵值变化轨迹,每一次‘错误’都短暂地提高了局部探索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讨论激烈而深入,充满了术语的交锋和灵感的碰撞。霍桑沉浸其中,思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贷款武道,校花表姐酸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曹家孟德)的经典小说:《贷款武道,校花表姐酸死了》最新章节...
- 474873字07-13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说好清心寡欲,七零老公却半夜敲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春光无限好多鱼)的经典小说:《说好清心寡欲,七零老公却半夜...
- 426903字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