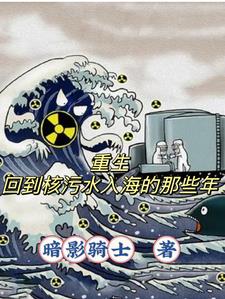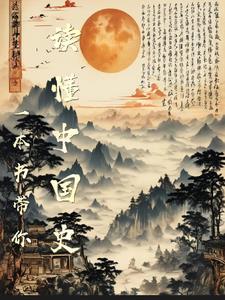第二十七章 苏轼沉浮人生:才华盖世,命运多舛
“文字狱”持续四月有余,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备受拷掠。他在《狱中寄子由》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甚至做好了“身后事”的安排。最终,因弟弟苏辙“愿弃官以赎兄罪”、旧党王安礼(王安石弟)力谏,加上曹太后(仁宗皇后)干预,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无实权,近乎流放)。
3.2 黄州:从“政治失意”到“文化哲人”的升华
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年(1080-1084),是苏轼人生的最低谷,也是其文学与思想的巅峰期。
(1)躬耕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
初到黄州,苏轼无官舍可居,暂寓定惠院;后得城东荒地五十亩,亲自垦荒,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中写道:“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这种“农夫”身份的转变,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的艰辛,也催生了对生命的敬畏。
(2)赤壁悟道:“天地与我并生”
1082年,苏轼两次游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并非三国古战场),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前赤壁赋》中,他与客问答:“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融入山水,最终得出“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结论——这正是庄子“齐物”思想与禅宗“空观”的融合。
(3)词风革新:“以诗为词”的突破
黄州时期的词作,彻底摆脱了传统词的“艳科”束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将自然风雨与人生困境打通;《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则是对儒家“修身齐家”与道家“逍遥游”的双重反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种“旷”,正是黄州岁月沉淀出的精神高度。
3.3 后贬谪时期:从惠州到儋州的“文化教化”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新党复起,苏轼被一贬再贬:1094年贬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再贬惠州(今广东惠州);1097年再贬儋州(今海南)。此时的他已近花甲,却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
惠州“瘴疠之地”,苏轼却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凝香笔)的经典小说:《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最新章节全文...
- 1821613字06-26
- 穿书师尊是个大反派
- 2926577字04-29
- 卡牌:重塑天地规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马铃薯三岁了)的经典小说:《卡牌:重塑天地规则》最新章节...
- 1308066字06-10
- 御鬼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鬼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3193750字06-25
- 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粨月)的经典小说:《我与老婆令人心梗的恋爱之旅》最新章节...
- 753612字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