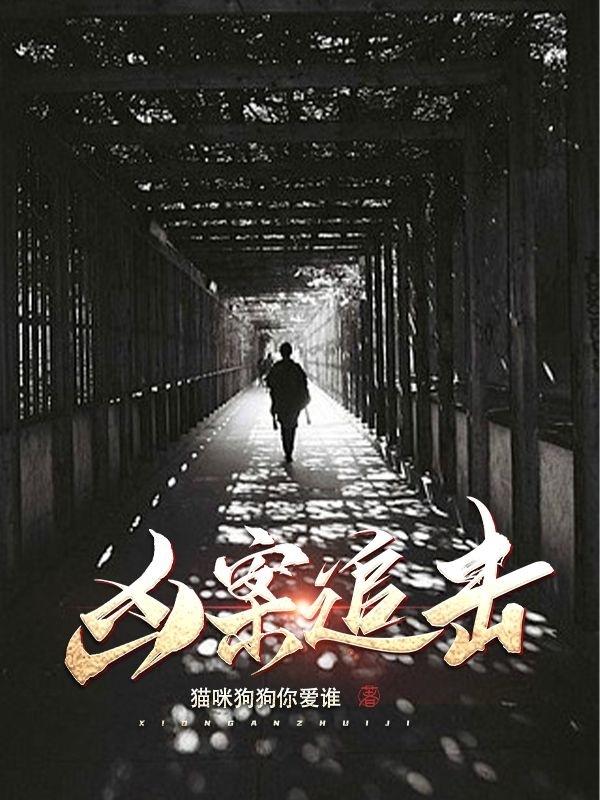第1641章 无畏擒龙(46)
砚之在静远堂住到第三百六十天的时候,恰逢冬至,院角的老桂树落了最后一片叶子,金黄的叶面上还沾着晨霜,像谁在叶尖撒了把碎银。她蹲在葡萄架下整理落叶时,发现挂在藤上的锦囊已经变得有些僵硬,红绳的颜色褪成了浅粉,像段被时光洗旧的记忆。“该把核取出来了,”老人抱着床棉被从西厢房出来,棉絮里裹着个小陶罐,“再捂就闷坏了,去年的桃核就是这么烂在布里的。”
砚之解开锦囊的红绳时,手指触到果核的纹路,比刚取出时更深了些,凸起的“静远堂”三个字在晨光里泛着油光,像被岁月磨亮的印章。老人把核放进陶罐,罐口塞着团新采的艾草,绿色的叶片在陶土上投下细碎的影,“得让它见见干风,”老人用麻绳把罐口扎紧,“等立春那天,就埋进东墙根,那儿背风,土温也合适。”
那天上午,村里的孩子们来送“暖核礼”,每人手里都攥着块烤红薯,热气腾腾的,把小脸熏得通红。“我娘说红薯皮能暖核,”梳羊角辫的小姑娘把红薯往陶罐旁凑了凑,甜香混着艾草的苦漫出来,“去年她埋土豆时就这么干,说‘热乎气能催醒睡着的芽’。”
老人笑着把红薯收在竹篮里,篮底铺着阿婉织的蓝布,烤焦的薯皮在布上印出褐色的斑,像幅抽象的画。“等会儿分给大家吃,”老人的手指在陶罐上轻轻敲着,发出闷闷的响,“核听见热闹,醒得才快。”
砚之把陶罐搬到窗台上,阳光透过玻璃照在罐身上,陶土的温度慢慢升起来,像给核裹了层看不见的棉被。她突然发现窗台的裂缝里卡着片银杏叶,是深秋时落下的,叶脉已经发黑,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扇形,和祖父《植物志》里夹着的那片几乎一样。“这是树在留念想,”老人往窗台上摆着盆水仙,“你看它把叶子卡得多牢,就像有些事,想忘都忘不掉。”
中午吃饭时,李婶带来了刚包的饺子,白菜馅的,饺边捏得像朵小小的腊梅,是用阿婉留下的木模压的,模子上的花纹已经被岁月磨得浅淡,却依然能看出花瓣的弧度。“我娘说冬至的饺子得捏花边,”李婶往醋碟里撒着姜丝,“这样才不会冻掉耳朵,当年阿婉姑娘就爱这么捏,说‘好看的饺子,吃着也香’。”
老人往砚之碗里夹着饺子,热气在两人之间凝成白雾,“你祖父在漠河时总说,”老人的筷子碰了碰醋碟,发出清脆的响,“北方的饺子得配蒜泥,南方的得就姜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味,换了就不对劲儿’。”
砚之咬开饺子的瞬间,白菜的鲜混着猪油的香在舌尖炸开,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_真是兔了【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江医生今天追回宋老师了吗gl》作者:真是兔了【完结】文案...
- 855093字09-09
- 错把恐怖游戏当恋综一不小心封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魔法怎么这么灵呀)的经典小说:《错把恐怖游戏当恋综一不小...
- 576059字12-25
- 鬼神老公,别太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朵野菊花)的经典小说:《鬼神老公,别太坏》最新章节全文阅...
- 1585078字07-29
- 我女友是侦探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萧梨花)的经典小说:《我女友是侦探》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01913字07-28
- 凶案追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猫咪狗狗你爱谁)的经典小说:《凶案追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177476字07-30
- 师妹你冷静点儿_这名字好【完结+番外】
- ( 内容简介: [百合] 《师妹你冷静点儿! gl》作者:这名字好【完结+番外】文案:...
- 226558字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