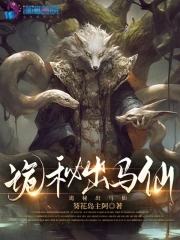第1638章 无畏擒龙(43)
桌上,篮子底铺着的蓝布绣着腊梅,针脚是村里的姑娘们一起绣的,“就像那花苞,得趁新鲜看,不然开败了可惜。”
老人往丝瓜上撒着盐,说要做凉拌丝瓜,“你祖父夏天最爱这口,”他的手在丝瓜上轻轻摩挲,像在给孩子擦脸,“说‘南方的绿得生吃,才够劲,不像北方的菜,得炖得烂烂的’。”
砚之帮忙摘丝瓜蒂时,发现蒂部的断口处渗出些透明的汁液,滴在青石板上,很快凝成了小小的珠,像给石板镶了颗翡翠。“这是植物的血,”老人用手指蘸了点汁液,在砚之的手心里画了朵小花,“你对它好,它就给你留着甜,藏在瓜肉里,藏在花苞里,从不骗人。”
下午,砚之继续续写祖父的书稿,写到“腊梅的香气能透骨,像北方的雪,看似清冷,却能渗进皮肉里”时,笔尖突然顿住了。她抬头望向花架,看见那道裂开的花苞缝里,鹅黄色的花瓣已经悄悄探了出来,像只胆怯的小兽,在风中轻轻颤动。“它要开了!”砚之的声音带着颤,像踩在棉花上。
老人放下手里的竹编活,慢悠悠地走过去,手里还捏着根没编完的藤条,藤条的弧度刚好能绕住花苞。“别急,”他用藤条在花架上搭了个小小的棚,“防着鸟雀啄,也挡挡过强的光,就像给姑娘撑把伞。”
砚之蹲在棚下看花瓣,发现花瓣的边缘带着极细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像阿婉绣品上的银线。她突然想起祖父书稿里的话:“最珍贵的美,往往藏在最细微的地方,得静下心来,才能看见。”
那天傍晚,天空突然烧起了晚霞,把整个院子染成了金红色。腊梅的花苞在霞光里泛着暖黄,裂开的缝更大了,能看见里面层层叠叠的花瓣,像颗被剥开的糖球。村里的孩子们放学来看花,书包往石桌上一扔,就围着花架蹲成圈,嘴里念着自编的童谣:“青包子,黄饺子,风儿吹,笑开了。”
老人往孩子们手里塞着米糕,米糕上的桂花在霞光里闪着光,像撒了把碎金。“慢点吃,”他的手抚过每个孩子的头顶,“等花开了,每人发块‘赏花糕’,用新采的桂花做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砚之坐在葡萄架下写书稿,晚霞透过叶隙落在纸上,把字迹染成了金红色,像祖父在为她的文字上色。她写:“晚霞是天空的情书,花苞是植物的承诺,都在等待一个温柔的回应。”写这句话时,笔尖的墨水突然变得浓稠,在纸上晕出片小小的云,像给文字盖了个晚霞的印章。
夜里的露水很重,砚之帮着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6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这崽也太好带了叭[...
- 458890字09-25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
- 时空长河的旅者
- 2757038字12-01
- 诡秘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葵花岛主阿)的经典小说:《诡秘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23251字12-25
- 从摸尸体开始的勇者玩家
- 4319567字11-23
- 超维度玩家
- 2680726字07-27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http://www.qibaxs7.com/modules/article/images/nocov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