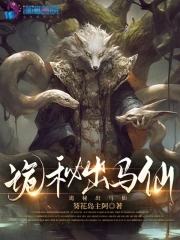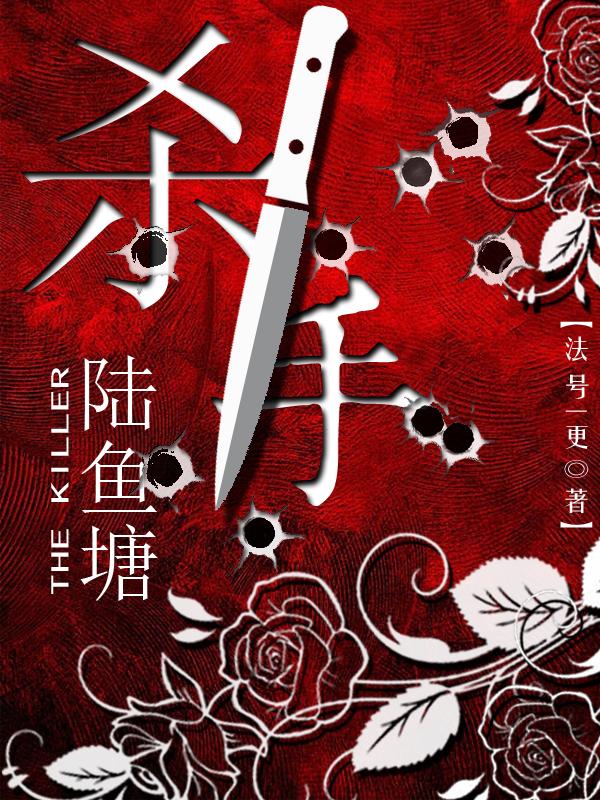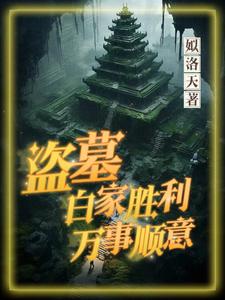第1638章 无畏擒龙(43)
人给花苞套上透气的纱袋,纱袋的边缘绣着圈细小的腊梅,是李婶和村里的绣娘们连夜赶制的。“这样既能透气,又能防着露水打湿花瓣,”老人的手指捏着纱袋的抽绳,动作轻得像在系蝴蝶结,“你祖父说‘好花得细养,就像好故事得细写,急了就失了韵味’。”
砚之摸着纱袋上的针脚,突然发现其中朵小腊梅的绣线是银色的,在月光下闪着微光,想必是老人偷偷绣的,他的指尖还留着银线的反光,像沾了点星光。“绣不好,”老人的耳尖有些红,“就是想给它添点亮。”
第二天清晨,砚之被鸟鸣声惊醒,是绣眼鸟的叫声,比往常更清亮,像在报喜。她跑到院里时,看见老人已经站在花架前,纱袋落在青石板上,里面的花苞已经半开,鹅黄色的花瓣舒展着,像只展翅的小蝴蝶,香气漫了满院,甜得发稠,混着桂花香,像把两个季节的香都揉在了一起。
“寅时开的,”老人的声音带着些微的颤,手里捏着片刚落下的花瓣,“我起来添柴,就听见‘噗’的一声,像谁轻轻叹了口气。”
砚之蹲下去闻花香,花瓣上的露珠滚进嘴里,甜得像蜂蜜,突然看见花芯里藏着只小小的蜜蜂,想必是被香气引来的,正趴在花蕊上,像在亲吻这迟到的绽放。“它比我们还急,”老人往旁边撒着花粉,“从村西头的油菜地飞来的,赶了半里地呢。”
那天上午,全村的人都来看花开,青石板上摆满了各家带来的礼物:老木匠做的小花盆,李婶蒸的桂花糕,孩子们画的腊梅图,连档案馆的人都特意赶来,给开花的腊梅拍了张“证件照”,说要放进“乡村植物档案”里,编号是“静远堂-001”。
老人把那坛埋在桂花树下的米酒挖了出来,开封时酒香混着花香漫出来,醉得人脚步发飘。“该给你祖父回信了,”老人往青瓷碗里倒酒,酒液里浮着整朵的腊梅花,“他等这杯酒,等了快四十年。”
砚之端着酒碗,看着花瓣在酒里轻轻打转,突然想起祖父书稿的最后一页空白,此刻终于有了答案。她从东厢房拿来书稿,在空白页上按下朵带着酒液的花瓣,印出个淡淡的黄痕,旁边写下:“静远堂的腊梅开了,带着北地的雪意,带着南枝的温润,带着所有的等待,开得正好。”
老人的手指抚过花瓣印,动作轻得像在抚摸蝴蝶的翅膀。“他看得见,”老人的眼角有些湿润,“就像当年他说的,‘花开花落,都是信使,会把话带到该去的地方’。”
中午的宴席摆在院里的桂花树下,石桌上摆满了菜,都带着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
-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这崽也太好带了叭[...
- 458890字09-25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
- 时空长河的旅者
- 2757038字12-01
- 诡秘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葵花岛主阿)的经典小说:《诡秘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23251字12-25
- 杀手陆鱼塘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法号一更)的经典小说:《杀手陆鱼塘》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431517字12-24
- 盗墓:白家胜利,万事顺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姒洛天)的经典小说:《盗墓:白家胜利,万事顺意》最新章节全...
- 14587370字07-01
![这崽也太好带了叭[娱乐圈]_苏九影【完结】](http://www.qibaxs7.com/modules/article/images/nocov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