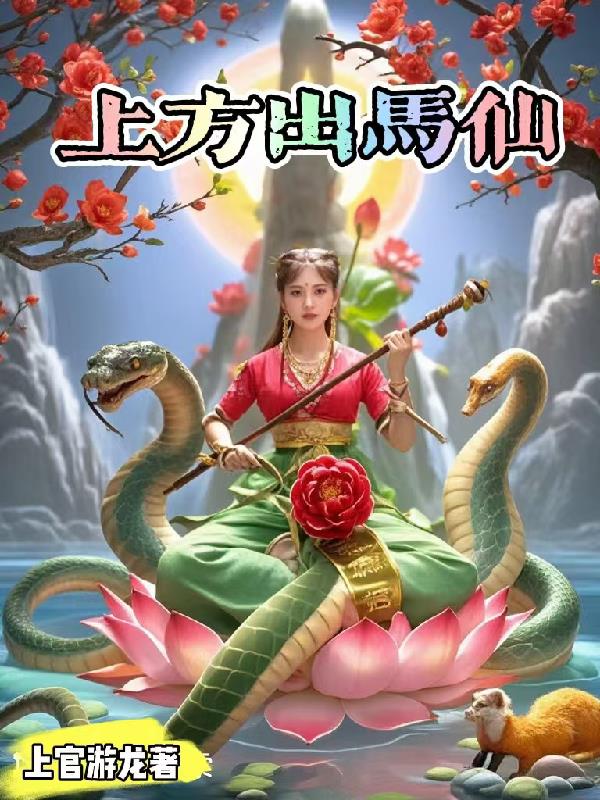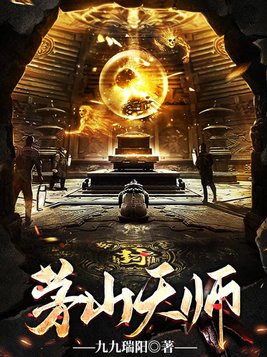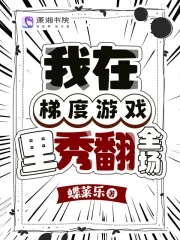第1638章 无畏擒龙(43)
的约定。”她写这句话时,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上,把字迹镀上了层金边,像祖父在为她的文字盖章。
中午,村里的老药农来了,背着个竹篓,篓里装着刚挖的何首乌,根茎上的纹路像无数个缠绕的“远”字。“我来给张老先生送点药引,”老药农把何首乌放在石桌上,眼睛却盯着花架上的腊梅苗,“这苗透着股灵气,怕是要提前开花。”
老人笑着递过杯桂花茶:“借您吉言,去年的枸杞就是听了您的话,结得比往年多。”
“那是您用心,”老药农的手指捏着何首乌的根茎,“养植物跟养人一样,得顺着性子来,急不得。你看这苗,知道往有光的地方长,多聪明。”
砚之看着两人说话,突然发现老药农的竹篓里露出半截书稿,是她前几天借给李婶看的,上面还贴着片桂花做的书签。原来这院里的故事,早就走出了静远堂的墙,像株蔓延的葡萄藤,枝枝蔓蔓都缠着村里人的生活,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串成了珍珠。
下午,砚之继续续写祖父的书稿,写到“漠河的雪落在腊梅上,像给花披了件白狐裘”时,笔尖突然顿住了。她起身去看腊梅苗,发现最顶端的花苞已经鼓了些,青绿色的外衣上透出淡淡的黄,像个害羞的姑娘,在风里悄悄梳妆。
“快了,”老人往花架旁的土里埋着鱼肠,用厚土盖严实了,“过不了十天,就能见着黄了。”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桂花的涩,“你祖父总说‘等待开花的日子,比开花本身更让人念想’。”
砚之看着花苞在风中轻轻摇曳,突然想起祖父书稿里的话:“最美的期待,是看着希望一点点长大,像看着孩子学步,每一步都藏着惊喜。”她回到书桌前,笔尖在纸上流畅地游走,把此刻的心情都写进了故事里,像给时光寄了封永远不会过期的信。
傍晚时,老人开始准备晚饭,灶台上的砂锅咕嘟作响,里面炖着腊梅根和排骨,香气漫了满院。“你祖父说,”老人往砂锅里撒着枸杞,红色的颗粒落在奶白的汤里,像撒了把碎玛瑙,“北方的冬天冷,得用些温补的食材,南方的湿,得用腊梅根去去潮气,这叫‘因地制宜’。”
砚之蹲在灶边添柴,看火苗舔着锅底,把两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像幅晃动的皮影戏。她突然发现灶膛的角落里藏着根炭笔,是祖父常用的那种,笔杆上刻着个极小的“远”字,和他书稿上的签名一模一样。
“这是他留下的,”老人往灶里添了块栗木炭,火苗腾起时映红了他的脸,“每次来静远堂,他都爱蹲在灶边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上方出马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上官游龙)的经典小说:《上方出马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15886字07-21
- 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宁修)的经典小说:《一个交警,抢刑侦的案子合适吗?》最新章...
- 6453499字05-09
- 茅山天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九瑞阳)的经典小说:《茅山天师》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166967字07-21
-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_一只花夹子【完结】
- ( 内容简介: [百合] 《和豪门大小 姐分手后》作者:一只花夹子【完结】文案:【原...
- 620878字09-09
- 劫天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浮梦流年)的经典小说:《劫天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24301574字07-29
- 我在梯度游戏里秀翻全场
- 我在梯度游戏里秀翻全场是由作者蝶莱乐著,免费提供我在梯度游戏里秀翻全场最新清爽...
- 2267834字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