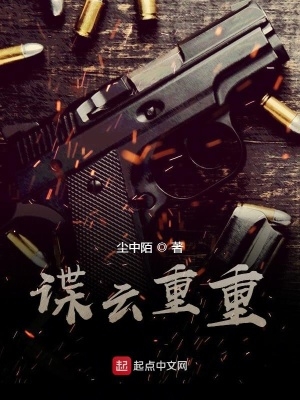四百二十三节 集体婚礼(五)
眉飞色舞,好像坐在云端里一样--这些人中颇有几个他的旧相识,亦有广州的世家旧族;有的人家,族中尚有亲人在明国当官,这会却都是一副从龙新贵的嘴脸。
世上果然是“名利”二字最为消磨人心!黎遂球自从和崔汉唐见了面之后,更为彷徨不安。崔汉唐的一席话其实也颇为打动了他:这世间的纷争不安,不外乎是百姓的太穷太苦了。他是饱读过史书的,知道改朝换代,大多是因为田土兼并而起。如今的大明亦是如此,百姓困顿不堪,只能铤而走险--就算没有髡贼,大明如今亦是岌岌可危。
若是澳洲人真有这崔道士所言的“提高生产力”的本事,这千百年的“破-立”轮回岂不是可以被打破?安居乐业亦不再是梦想。
然而他再一想,觉得崔道长说得未免也太玄了。世上哪有点石成金之事?纵然他们有些秘法,能让田地产量提高,那也有限的很,怎么可能惠及天下,更别说土地这东西都是天生的,总不能凭空多出来吧?
黎遂球为这件事苦恼了许久,他意识到自己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地步。效忠大明原没有什么好疑惑的;然而澳洲人到了广州的表现和他们过去在琼州的声誉,让他意识到,澳洲人或许有种种不是,也或许喜欢吹牛骗人,但是至少眼下百姓们是得了他们的好处的,欢欢喜喜的当起了“大宋顺民”。而他要效忠的大明,却对百姓们没什么吸引力。说来也是:他黎遂球是受了“国恩”的,百姓们又得了什么好处呢?
正当他为这些事彷徨的时候,集体婚礼的消息通过报纸又传递到了他的眼前。他不得不佩服澳洲人办报纸这个思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不是赞成。只要不想消息闭塞,就得忍受无休止的消息的潮水。而这些信息会悄无声息的改变一个人的看法--这点,黎遂球已经领教到了。从他们入城伊始的的“汉贼不两立”,到“髡贼治理亦有可取之处”,再到最近的“澳洲人得民心”……黎遂球自己都意识到了这种转变远比崔道长的喋喋不休,堆砌名词来得厉害的多。
眼前这桩集体婚礼亦然。黎遂球对此的观感和宋应升并无二致:好事,但是小题大做。但是连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军师王妃
- 2641772字11-17
- 五雀(H)
- 334269字07-26
- 谍云重重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尘中陌)的经典小说:《谍云重重》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4321769字07-27
- 亮剑:开局助李云龙获意大利炮
- 2093834字12-04
- 完蛋,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 3922742字07-29
- 大明枭
- 1139747字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