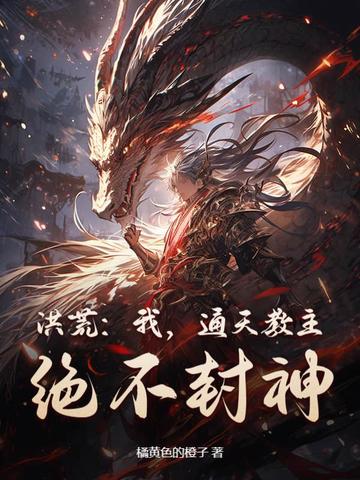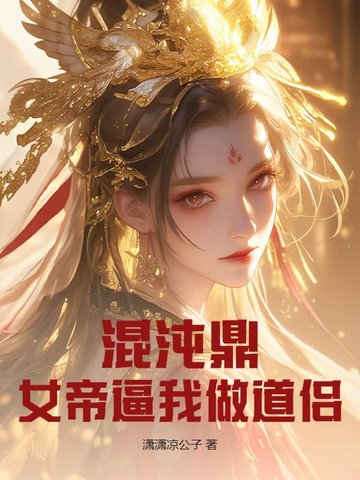长篇小说《木黄会师》第九集:木根坡重逢
1934年10月23日的黔东,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像浸了墨的棉絮,沉甸甸压在木根坡的山脊上。郭鹏攥着怀表的手指沁出冷汗,铜壳子上的刻度早已被体温焐得模糊——按照约定,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本该在丑时抵达。五十团的战士们蜷缩在岩石后,枪托上的露水顺着指缝滑进袖口,冰凉刺骨。
“团长,你听!”通信员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风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号音,像被揉皱的纸条在风中抖动。郭鹏猛地直起身,那旋律他太熟悉了——《战斗号角》的变调,是六军团在湘赣根据地时就用的联络信号,每个升调都比标准谱高半个音,那是任弼时亲自定下的暗号。
司号员小李的嘴唇在颤抖,黄铜号嘴磕得牙齿发响。他深吸一口气,腮帮子鼓得像含着枚野果,变调的号音骤然划破夜空。三短两长,这是“发现友军,请求确认”的信号。山坳那头的号声停顿片刻,随即传来同样的回应,只是尾音带着难以察觉的哽咽。
“吹集合号!”郭鹏扯开嗓子,声音劈得像被枪子儿擦过。战士们纷纷从掩体后爬起来,有人慌忙系紧松开的绑腿,有人把刺刀往石头上蹭了蹭,寒光在月光下一闪而过。五十团沿着被马蹄踏软的山路疾行,灌木丛里惊起的夜鸟扑棱棱掠过头顶,翅膀带起的风里混着硝烟的味道。
坝溪的溪水在石缝间打着旋,周球发正用刺刀削着竹片。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的马蹄灯挂在老榕树上,昏黄的光晕里,他腕骨上的旧伤又在隐隐作痛——那是去年在潜江战斗中被手榴弹弹片划的。听见号声时,竹片“啪”地断成两截,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向溪边,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是六军团的号!”炊事班长老王举着铜锅跑过来,锅里的糙米还在晃悠,“我就说嘛,贺军长算的时辰准没错!”周球发没接话,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对岸的山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竹筒——里面装着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炒盐,他一直想留给哥哥周球保。
两支队伍在溪滩上相遇时,谁也说不清是谁先扑过去的。红二军团的战士们举着马蹄灯,光柱像探照灯似的扫过对方的脸,有人突然抱住个六军团的小个子战士嚎啕大哭——那是他在洪湖苏区时的同乡,三年前分开时还没他胸口高,如今却能扛起机枪了。
“可算见着活人了!”六军团的一个老兵抓住件灰布军装就不放,那衣服上还沾着湘江的泥浆,“我们从界首渡口过来时,江里漂的都是战友的绑腿……”话没说完就被红二军团的战士捂住嘴,“别说这些,先喝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同穿:举国随我开发异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沈见新)的经典小说:《同穿:举国随我开发异世界》最新章节...
- 899710字07-26
- 洪荒:我,通天教主,绝不封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橘黄色的橙子)的经典小说:《洪荒:我,通天教主,绝不封神!...
- 788049字07-27
- 修仙:从杂役开始模拟长生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洛无书)的经典小说:《修仙:从杂役开始模拟长生路》最新章...
- 350270字07-27
- 完美世界之魔帝
- 2524921字11-23
- 混沌鼎:女帝逼我做道侣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潇潇凉公子)的经典小说:《混沌鼎:女帝逼我做道侣》最新章...
- 380688字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