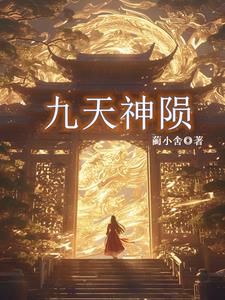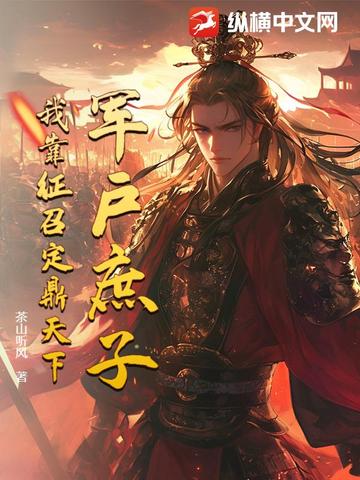第一百九十七 双宝联动:蒸汽制盐机与内陆探路的契机
都在抖。
林远让人测试了水样,盐度足够。他当即答应派王工匠的徒弟去帮忙,条件是“雪松部落得派向导,带我们的人往更北的地方走”。交易达成那天,雪松人杀了头鹿,和雾湾的士兵、红鲑部落的人一起围着篝火吃肉,王工匠的徒弟正给他们讲蒸汽管的原理,虽然鸡同鸭讲,却没人觉得不耐烦。
新明区的王守仁很快收到了内陆勘探的消息,回电里附了张《北美资源预想图》,用红笔圈出几处“可能有铁矿”的区域:“按大明的经验,有煤有盐的地方,多半藏着铁。让勘探队多留意红棕色的石头,那是铁的记号。”他还特意嘱咐,“探路时多带铁针、小铁刀当礼物,部落人认这些实在东西。”
林远把王守仁的图给勘探队的人看,又给每个队员配了本《双语对照手册》,里面记着“铁矿”“煤层”“友好”“危险”等关键词的印第安语发音。赵武主动要求带队:“我跟着林大人从南美打到北美,这点路不算啥。”他选了五个老兵,配上三支步枪,还有鲑生推荐的红鲑部落年轻人“煤蛋”——这孩子不仅会采煤,还认得不少内陆植物,知道哪些能吃、哪些有毒。
勘探队出发那天,雾湾的蒸汽船鸣笛送行。煤蛋背着工具包,腰里别着王工匠给的小煤铲,说要“找到比红鲑河更好的煤和盐”。林远站在码头,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河谷尽头,突然觉得这场景很熟悉——就像当初从新明区出发去安济港,从安济港跳到雾湾一样,每一步都踩在“资源”与“信任”的节点上。
蒸汽制盐机的轰鸣声成了红鲑盐泉的日常。白花花的精盐堆满货栈,等着安济港的船来运;采出的煤除了供炮艇和盐机用,还能换更多铁网、步枪和新明区的棉布。有次林远看到瘸腿首领穿着件玛雅棉布做的袍子,正指挥人往船上装盐,袍子上绣着红鲑图案,针脚是用铁针缝的,细密又平整。
王工匠在盐泉旁盖了间“铁匠铺”,教部落人把废铁打成小工具——鱼钩、锥子、小斧头,换他们采来的煤。鲑生的弟弟“盐粒”学得最认真,能把铁打成像精盐一样薄的铁片,王工匠说这孩子“有红炉匠的天赋”。
这夜,林远在灯下翻看勘探队发回的第一封简报。上面画着一条大河,旁边标着“能行船”,还有个歪歪扭扭的“铁”字,旁边画了块红石头。他拿起笔,在《北美拓殖图》上,从雾湾往内陆画了条虚线,终点落在那个“铁”字上。
窗外,蒸汽制盐机的汽笛声和远处的煤窑号子混在一起,像支奇特的歌谣。林远知道,有了蒸汽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本来只想带崽,结果全师门都跟我混
- 284359字07-23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九天神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蔺小舍)的经典小说:《九天神陨》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710233字07-27
- 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茶山听风)的经典小说:《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最新章...
- 611379字07-26
- 血炼妖帝
- 2663288字07-25
- 魔法没前途,还得靠修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丝余半)的经典小说:《魔法没前途,还得靠修仙》最新章节全...
- 700732字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