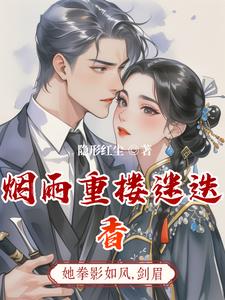第195章 烽火川魂:锦江潮涌归故里
船上坐着群白发老人,都是归乡的川军老兵和他们的后代,手里捧着鲜花,对着江面轻轻撒下。
92岁的张铁山坐在船头,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挂着勋章。他的独臂微微抬起,指着远处的码头:"当年,俺们就是从那儿出发的,船开的时候,锦江的水是黄的,像掺了高粱酒。"阳光照在他脸上,皱纹里仿佛还藏着烽火的影子。
旁边坐着王念军,手里拿着父亲的钢笔帽,对着江面说:"爹,锦江的水还是往东流,跟您说的一样。广安的织锦坊还在,您的锦帕,成了国宝。"江风拂过,带着水汽,像有人在轻轻应和。
游船行至少城公园附近,岸边的石碑前摆满了鲜花。石碑上的名字经过多次修复,金粉重新填过,在阳光下闪着光。有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指着"陈满仓"的名字说:"宝宝看,这是英雄爷爷,是他让我们能坐游船,看锦江。"
张铁山让后代把自己的军功章放在石碑前,跟那些名字摆在一起。"俺们这些活着的,只是替牺牲的弟兄们,多看看这太平盛世。"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他们的名字,得刻在锦江的石头上,刻在四川的山上,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游船返回码头时,夕阳把江面染成了金红色。岸边突然响起川剧的唱腔,是《出师表》里的句子:"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唱腔混着江涛声,像350万川军的呐喊,穿过八十年的时光,在和平的天空下回荡。
张铁山望着满江的金波,仿佛看见无数草鞋踏过水面,无数油纸包在江面上漂,无数锦帕在风中舞。那些穿着单衣的川军将士,正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笑着说:"看,这就是我们用命守护的家乡,河水清,稻花香,娃娃们都在笑。"
如今,在四川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川军的印记:成都的川军抗战纪念馆里,那只磨破的草鞋总有人驻足;自贡的盐业历史博物馆里,李灶保的盐菜罐摆在显眼的位置;广安的蜀锦博物馆里,王文书的家书复印件前,总围着听故事的孩子。
这些印记告诉我们:350万出川的川军,从未真正离开。他们化作了锦江的浪花,化作了峨眉山的云雾,化作了四川大地上的每一粒泥土。当风吹过稻田,那沙沙声是他们在说"今年的收成好";当雨落在锦帕上,那滴答声是他们在讲"家乡的姑娘织得巧";当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那欢笑声里,有他们未说完的牵挂,未唱完的歌。
这就是川军的魂——是码头绳结里的乡愁,是雪地灶火里的血性,是战壕家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0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红孩儿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番茄大世界)的经典小说:《红孩儿传》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705733字06-30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烟雨重楼迷迭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隐形红尘)的经典小说:《烟雨重楼迷迭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874424字07-21
- 咸鱼穿成豪门后爸在娃综爆红
- 咸鱼穿成豪门后爸在娃综爆红章节目录,提供咸鱼穿成豪门后爸在娃综爆红的最新更新章...
- 898950字07-17
- 我打律者?真的假的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法厄同)的经典小说:《我打律者?真的假的》最新章节全文阅...
- 1692193字06-18
- 斗罗:超A天狐竟是千道流白月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会说恭喜发财的猪)的经典小说:《斗罗:超A天狐竟是千道流白...
- 796516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