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锦江潮涌:一枚导弹的巴蜀胎记
川剧院的新编剧目《火鸟飞天》,把红旗七号的研制故事搬上了舞台。当“陈岚”在台上用乐山话念叨“雾里的弹道像峨眉山的路,绕弯子也要往前冲”时,台下总会响起会心的笑声。最震撼的是结尾:川剧演员吐出的火焰化作虚拟的导弹尾焰,在全息投影里直冲云霄,照亮了背景中重庆的吊脚楼、成都的茶馆、绵阳的群山。
“我们加了段‘帮打唱’,”主演说,“老辈人搞科研,不就是‘帮’着搭把手,‘打’碎拦路虎,‘唱’着不服输的歌吗?”有位当年的算法工程师看完戏,在后台找到演员,红着眼眶说:“你们把我们没说出口的苦,都唱出来了。”
锦江的夜,总带着水汽的温柔。岸边的茶桌旁,几位老人正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穿蓝布衫的是退休车工,他的指节在桌上划出一道弧线:“红旗一号的弹道,就像府南河的弯道,看着缓,其实后劲足。”戴眼镜的老教授摇摇头,用指尖敲出急促的点:“红旗七号得像嘉陵江的险滩,快、准、狠,不然抓不住低空目标。”
争论声惊动了邻桌的年轻人,他们凑过来听,有人突然说:“现在的红旗-16FE,该像沱江汇进长江,又稳又远吧?”老人们都笑了,蓝布衫老人给年轻人倒了杯茶:“你说对了。但不管是哪条江,源头都在蜀山——就像不管哪款导弹,根都在咱们四川人的骨子里。”
八、算珠与代码的接力赛
电子科技大学的档案馆里,藏着个褪色的帆布包。包里装着五十多把算盘,有的缺了珠子,有的边框开裂,算珠上的指痕却清晰可辨。标签上写着:“1960-1970年,用于红旗导弹弹道计算。”这些算盘,是“代码时代”的老祖宗。
“当年算一组弹道数据,得三个人轮着打,打坏了就换一把,”档案馆管理员说,“现在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上亿次,但我们特意把这些算盘展示出来,就是想让学生知道,‘快’不是唯一的标准——当年的人用慢功夫,算出了不慢的进度。”
35岁的赵宇办公室里,摆着两样“传家宝”:祖父王大贵磨秃的游标卡尺,和自己编写的第一行导弹制导代码打印件。“祖父的卡尺能量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我的代码能算出0.1秒的误差,”他笑着说,“工具变了,但‘较真’没变。”
有次调试算法,赵宇团队卡了三个月。某天深夜,他翻出祖父的工作笔记,看到上面用铅笔写着“零件要像腌腊肉,多道工序才入味”,突然开窍:“我们太追求‘快’,忘了‘细’。”他们借鉴老工匠“分步打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865466字07-21
- 初夏的函数式
- 初夏的函数式章节目录,提供初夏的函数式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31514字07-21
- 攻略成功后,被疯批缠上了
- 415606字07-19
-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
- 2740951字07-19
- 超神:我以虚空万藏解析诸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云吞的京京兽)的经典小说:《超神:我以虚空万藏解析诸...
- 636518字07-23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18771822字07-21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60/62760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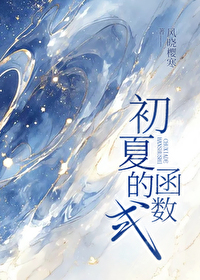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75/62775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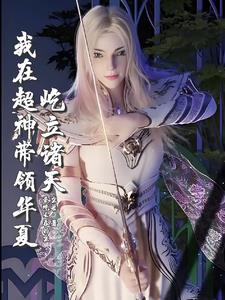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3/63060/63060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