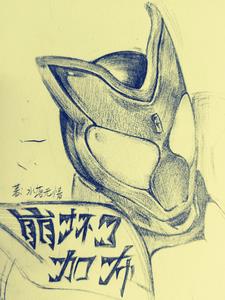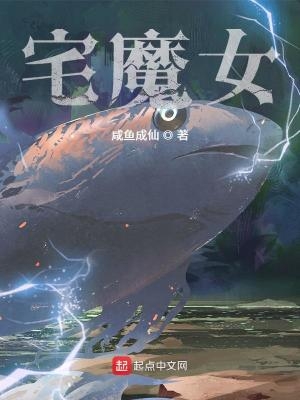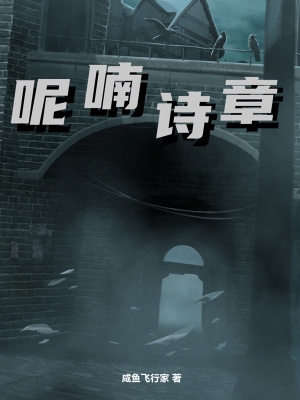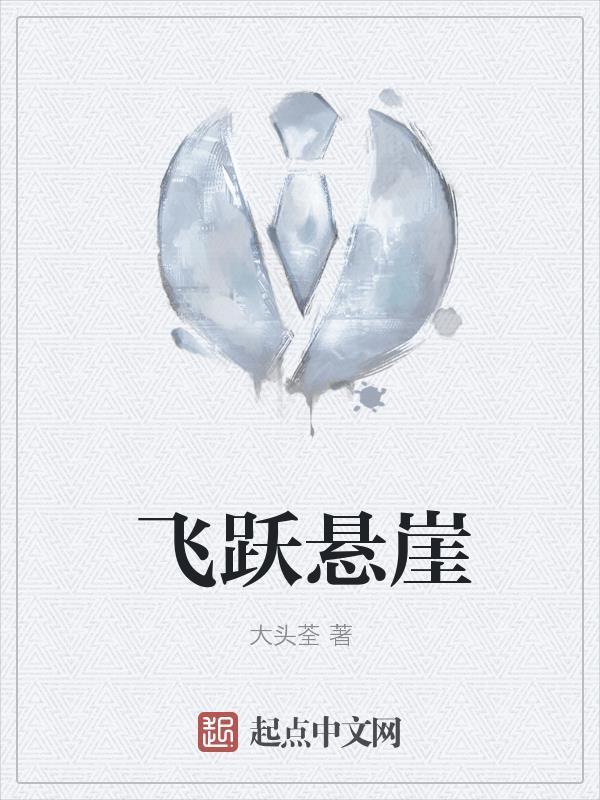第182章 巴蜀烟盒里的旧时光
的人说,那是加了黄龙的高山草甸的气息,抽起来有“仙气”。我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家乡》,还照着烟盒上的图案,用蜡笔描过一幅九寨沟的画,蓝的海、绿的树、白的瀑布,老师在评语里写:“画得像真的一样。”其实我从没去过,全靠烟盒上的色彩撑着胆子想象。
烟盒还藏着旅人的心事。有次在松潘古城的客栈,见个背包客在烟盒背面写日记,字迹被高原的风吹得发飘:“2005年7月,在五花海遇见穿红裙的姑娘,她的笑比烟盒上的海还蓝。”烟盒后来被他夹在游记里,成了最鲜活的注脚。
九寨沟烟的退场,像一场慢慢褪色的梦。后来旅游市场的伴手礼越来越多样,牦牛肉、藏茶、唐卡成了新宠,烟渐渐被挤到了货架角落。2010年再去九寨沟,商店老板说:“现在游客不爱带烟了,说不健康,都买青稞饼。”
前阵子整理书柜,翻出母亲当年带回来的烟盒,五花海的蓝已经发灰,像被岁月蒙上了一层纱。想起当年对着烟盒憧憬远方的自己,忽然明白,消失的不只是烟,还有那个拿着烟盒就能想象世界的年纪——那时的美好,简单得像烟盒上的画,蓝是蓝,绿是绿,白是白,没那么多弯弯绕。
六、攀西的阳光落了,矿山里的烈
攀西牌的烟,带着川西南河谷的烈阳味。烟盒上的攀枝花红得像团火,花瓣边缘泛着金,花底下印着行黑字:“凉山·攀枝花”,字的笔画里都透着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攀西地区,这抹红是矿山、河谷、彝家村寨里最硬的“通货”。
表哥是攀枝花矿山的老矿工,他说:“在井下,攀西就是‘强心针’。”下井前抽一支,“壮胆”;升井后抽一支,“压惊”。矿工们的烟盒,边角总带着煤渣的黑,却被手心的汗浸得发亮,像裹着层釉。烟盒里的烟丝,粗得像麻绳,却金黄发亮,“那是用金沙江畔的烟叶做的,晒足了180天太阳”。
矿山的宿舍里,烟盒是“社交货币”。新来的矿工递上攀西,老工人接了,才算“认了你”;谁家里有事,大家凑钱买几条攀西当礼,“比送酒实在”;连彝族的小伙子追姑娘,都会在烟盒里塞朵索玛花,“烟是烈的,花是柔的,姑娘才喜欢”。
有次矿里出了点小事故,表哥和工友们被困在井下两小时。黑暗里,他摸出最后一支攀西,烟盒“啪”地弹开,火光在十几双眼睛里跳。烟在粗糙的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气,烟丝燃尽时,救援的灯光也照了进来。“那烟味,比啥都提神,”表哥说这话时,指节在烟盒上敲了敲,像在敲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崩坏三:加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水落无情)的经典小说:《崩坏三:加布》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216751字07-21
- 小娘子
- 194457字11-04
- 宅魔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咸鱼成仙)的经典小说:《宅魔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6563804字07-13
- 呢喃诗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咸鱼飞行家)的经典小说:《呢喃诗章》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3370549字07-21
- 她不可妻
- 她不可妻章节目录,提供她不可妻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14796字09-28
- 飞跃悬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大头荃)的经典小说:《飞跃悬崖》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5364649字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