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川西藏地的分支印记:巴蜀边缘的藏族源流
引过来,两人坐在野花丛中,把名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
每年夏天,若尔盖的“雅敦节”是安多人的狂欢。“雅敦”意为“夏日盛宴”,草原上会搭起数百顶帐篷,像突然冒出的一片白色蘑菇。最热闹的是“赛马会”,但安多的赛马不像康巴那样追求速度,而是比“马技”——骑手要在马背上做“拾哈达”“倒挂金钩”的动作,还要边骑马边唱拉伊,歌声不跑调、动作不变形才算赢。姑娘们则聚在帐篷前“赛绣”,她们的“邦典”围裙上要绣满格桑花、雪莲花、雄鹰,谁的针脚最密、颜色最艳,谁就能得到老人们的“哈达祝福”。
安多人对信仰的表达带着游牧的洒脱。他们的玛尼堆不像卫藏那般规整,石头是随手从河边捡的,有圆的、扁的、带花纹的,只要刻上六字真言就堆在路边,路过的人都会添一块石头,让玛尼堆像草原一样慢慢生长。经幡也不是刻意挂的,风把布吹到哪里,就在哪里系上——树梢、桥墩、甚至牛角上,都可能飘着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经幡,那是天空、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的象征,风每吹动一次,就等于念了一遍经文。
阿坝县的郎依寺是安多藏区的苯教圣地,寺里的法事充满神秘色彩。每年农历六月,“祭山节”上,喇嘛们会头戴用彩布和牦牛毛做的“面具”,面具上画着山神的眼睛和獠牙,跳着模仿牦牛奔跑、雄鹰飞翔的“神舞”。他们的舞步沉重而有力,每一步都踩在鼓点上,仿佛在唤醒沉睡的山神。广场上的信徒们捧着青稞酒,等喇嘛跳完舞,就将酒洒向天空,酒珠在阳光下像碎金一样落下,据说这样能让山神闻到酒香,保佑草原不遭冰雹。
安多人与草原的生灵有着天生的默契。他们从不随意猎杀飞鸟,说“鸟是天的使者”;也不轻易砍伐活树,认为“树里住着山神的孩子”。冬天雪大时,他们会在帐篷周围撒盐巴,吸引饥饿的黄羊来觅食;春天母鹿产崽时,放牧的人会绕着鹿群走,不打扰它们的安宁。有个老牧民说:“草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让她疼。”
如今,安多人的生活里多了些新东西——摩托车代替了部分马队,太阳能板在帐篷顶上闪闪发光,年轻人用手机直播草原的日出。但当夕阳西下,他们依然会在帐篷前点燃牛粪火,老人给孩子讲“格萨尔王赛马夺魁”的故事,火苗在他们脸上跳着,像在重复着千百年的时光。草原上的风还是那么长,吹过经幡,吹过马头琴,吹过安多人的歌声,把游牧的诗意,吹向更远的远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6页 / 共10页
相关小说
- 初夏的函数式
- 初夏的函数式章节目录,提供初夏的函数式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31514字07-21
- 菟丝美人[快穿]
- 菟丝美人[快穿]章节目录,提供菟丝美人[快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90800字07-21
- 卿为佳人
- 卿为佳人章节目录,提供卿为佳人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406508字07-18
- 攻略成功后,被疯批缠上了
- 415606字07-19
-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
- 865466字07-21
-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
- 2740951字0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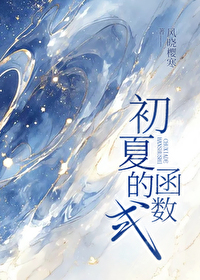
![菟丝美人[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3/63070/63070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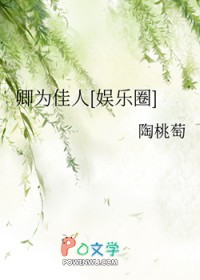

![我怀了你的孩子![穿书]](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60/62760s.jpg)
![后妈文的炮灰小姑[八零]](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75/62775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