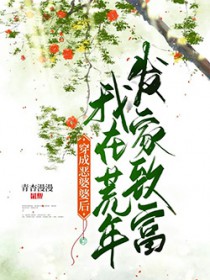第177章 四川话里的儿:舌尖上的小团圆
的语言魔法
四川人给动物起名字,总爱用“儿”字勾出亲昵。巷子里追猫的孩童喊:“三花妹儿,莫跑那么快!”那“妹儿”的“儿”字带着宠溺,连猫尾巴都翘得温柔。乡下的放牛娃甩着响鞭:“牛儿,走快点儿,坡上的草正嫩!”“牛儿”的“儿”字裹着青草香,牛儿甩尾的动作都轻快了几分。
植物在四川话里也被“儿”字点化得活泼。青城山的老道指着药圃:“这味是夏枯草儿,清热退火最好。”“夏枯草儿”的“儿”字像给草药披上了件薄纱,连苦味都淡了。菜市场里,卖花的阿婆握着几支黄桷兰:“买串花花儿嘛,香得很!”“花花儿”的“儿”字让白玉兰瞬间有了少女的娇羞。
更绝的是抽象概念的“儿化”。老中医把脉后沉吟:“你这脉相儿有点虚,要多进补。”“脉相儿”的“儿”字把无形的脉象说成了可触摸的物件。麻将桌上,输钱的大爷自嘲:“今天手气孬,输了个精光光儿。”“精光光儿”的“儿”字让懊恼化作了一声叹息,混着茶碗里的茉莉花香飘散。
(四)地域密码里的“儿化图谱”
川西坝子的“儿化”带着水的灵动。成都人说“汤圆儿”,“儿”字在舌尖轻轻一弹,仿佛能看见糯米团在沸水里打滚。温江的花农摘玫瑰:“这朵花儿开得周正,插瓶儿头好看。”“瓶儿头”的“儿”字把花瓶说成了花朵的闺房。
川南丘陵的“儿化”多了份山的硬朗。自贡盐井边,挑夫们喊着号子:“嘿哟,把这坨盐巴儿抬稳当!”“盐巴儿”的“儿”字带着盐粒的粗粝,混着汗水砸在青石板上。泸州老窖的酒窖里,酿酒师傅尝着新酒:“这坛酒儿窖香足,再放两年更醇。”“酒儿”的“儿”字裹着酒糟香,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
川东山地的“儿化”又添了几分麻辣。重庆火锅店里,食客喊:“老板,加份毛肚儿,七上八下那种!”“毛肚儿”的“儿”字带着牛油的滚烫,连辣度都翻倍。奉节脐橙园里,果农摘下橙子:“这个柑儿甜得很,不酸牙。”“柑儿”的“儿”字像橙子的汁水,在舌尖炸开甜蜜。
(五)时光褶皱里的“儿化记忆”
奶奶的针线筐里总装着“顶针儿”。她戴着老花镜纳鞋底:“这个顶针儿用了三十年,包浆都出来了。”“顶针儿”的“儿”字磨得发亮,像奶奶手上的老茧。爷爷的旱烟袋挂在门楣上:“把烟杆儿递给我,抽袋叶子烟解乏。”“烟杆儿”的“儿”字沾着陈年烟叶香,在暮色里飘成一缕乡愁。
老照片里的“儿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朕当外室那些年
- 809304字07-19
- 龙族:吞噬权柄!无限获取言灵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野狐快哉风)的经典小说:《龙族:吞噬权柄!无限获取言灵》...
- 621177字07-19
- 废土第一卧底
- 废土第一卧底章节目录,提供废土第一卧底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25440字07-18
- 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
- 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章节目录,提供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的最新更...
- 2917316字07-18
- 综漫:从问题少年到根源魔法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芥梦)的经典小说:《综漫:从问题少年到根源魔法师》最新章...
- 500661字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