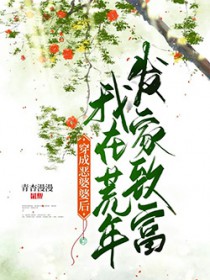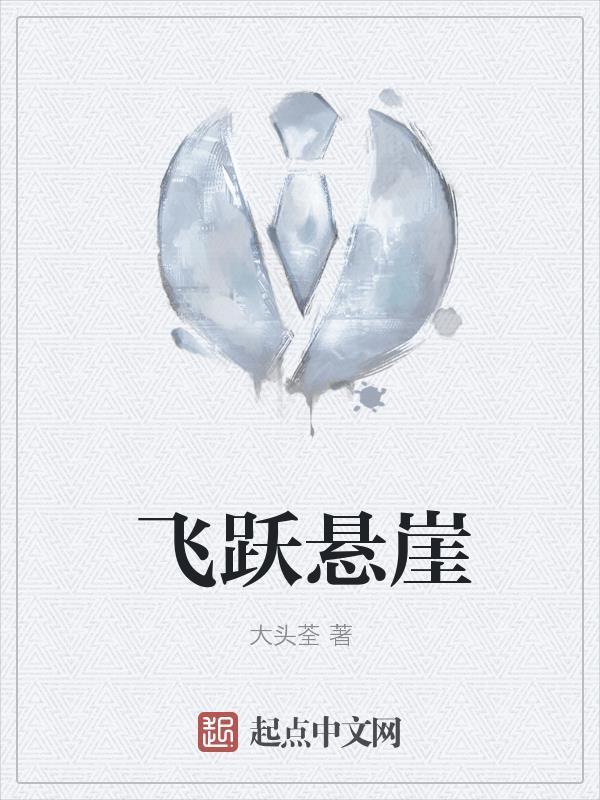第177章 四川话里的儿:舌尖上的小团圆
人儿,糖人儿,好看又好吃!”那“糖人儿”的“儿”裹着糖香,从街角飘过来,勾得细娃儿们拽着大人的衣角不肯走。
修鞋的师傅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锥子:“这个鞋跟儿松了,我给你钉紧点。”补衣服的嬢嬢眯着眼穿线:“袖口儿磨破了,我给你打个补丁,看不出来的。”他们说的“鞋跟儿”“袖口儿”,加个“儿”,仿佛那些磨损的地方也变得不那么刺眼了,透着点“小问题,包在我身上”的笃定。
巷子里的麻将声里,也藏着“儿”。“碰!”“杠!”“幺鸡儿!”——幺鸡是一条,加个“儿”,牌桌上的紧张就松了半分,仿佛那只红冠子的小鸡,扑腾着翅膀从牌堆里跳出来,逗得满桌人笑。赢了钱的大爷数着票子:“今天手气好,赢了几十块儿。”“块儿”比“块”多了点轻飘飘的得意,像揣在兜里的不是钱,是点小确幸。
最有意思的是四川话里的“角儿”,不光指角色,还能指零钱。“给我找两个角儿”,就是要两毛零钱;“这个角儿揣在兜里要掉”,说的是硬币容易丢。有次坐公交,投币时掉了个五角硬币,司机师傅笑着说:“这个角儿还挺调皮。”——把硬币叫“角儿”,加个“儿”,连掉钱的懊恼都淡了,仿佛那硬币不是丢了,是自己跑出去玩了,带着点孩子气的宽容。
小时候在巷子里追猫,猫钻进了“洞洞儿”——墙根下的小洞,加个“儿”,就成了猫的秘密基地。喊小伙伴回家吃饭,站在院门口喊:“三娃儿!回家了!”那“儿”字在巷子里拐几个弯,钻进各家各户的窗户,比什么都管用。有次隔壁王爷爷喊他孙子:“狗蛋儿!你妈给你买了冰棍儿!”“冰棍儿”的“儿”带着凉意,从舌尖滑到心里,连夏天的热都消了大半。
四川话的“儿”,在街巷里滚得越久,就越有烟火气。它不像书面语那样端着,也不像外地话那样生分,就像巷子里的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光滑,踩上去踏踏实实的。你说它是口音也好,是习惯也罢,说到底,是四川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人”的模样——不用装,不用演,把那些寻常物件、琐碎日子,都用“儿”字轻轻一裹,就裹出了家的味道。
五、时光里泡软的“儿”
奶奶九十多岁了,说话漏风,却依然把“豆”叫“豆儿”。有次她指着桌上的红豆,颤巍巍地说:“红豆儿……煮稀饭……”我凑近听,那“儿”字含在嘴里,像颗化了一半的糖,含糊却温暖。她年轻时在乡下种豆子,收工回来就坐在门槛上捡黄豆,“这个黄豆儿饱满”“那个绿豆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9页
相关小说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小娘子
- 194457字11-04
- 龙族:吞噬权柄!无限获取言灵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野狐快哉风)的经典小说:《龙族:吞噬权柄!无限获取言灵》...
- 621177字07-19
- 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
- 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章节目录,提供穿成恶婆婆后我在荒年发家致富的最新更...
- 2917316字07-18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飞跃悬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大头荃)的经典小说:《飞跃悬崖》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5364649字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