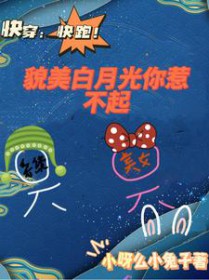第166章 元稹: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
官印拓片和复原的书房,讲述元稹的生平。最让人揪心的是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复制的“疟疾药方”和粗陶药罐。药方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元稹病中所书:“青蒿一束,水三升,煎至一升,温服”,旁边的说明牌写着“据考证,此为元稹在通州治疗疟疾时所用方剂,比《本草纲目》记载早近千年”。药罐的内壁结着褐色的垢,仿佛还能闻到当年苦涩的药味。展台前,常有老人指着药罐叹息:“元九公在咱这儿,真是遭了罪啊。”
第二展厅“诗韵通州”是纪念馆的灵魂所在。这里没有冰冷的文物,只有“活着的诗”。一面墙被设计成“诗笺墙”,贴满了仿唐代的麻纸诗笺,上面抄录着元稹在通州写的78首诗。《戛云亭》的诗笺旁,挂着一幅戛云亭的水墨画,画中茅屋依山而建,州河在脚下蜿蜒,与诗里“危亭绝顶四无邻”的意境完美重合。另一处展台还原了“元白唱和”的场景:两张相对的书案,分别摆着元稹与白居易的诗集,案上的烛台燃着仿真蜡烛,光影摇曳中,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深夜,两个贬谪他乡的诗人正借着烛光,把思念写进诗行里。
最动人的是“百姓说元九”互动区。墙上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达州人的采访:卖登高馍的大妈说“元九公让咱达州有了名气”;退休教师说“教学生读他的诗,就是教他们做人要有骨气”;小学生举着自己画的凤凰山说“长大要像元九公一样写很多诗”。旁边的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稚嫩的笔迹:“元稹哥哥,你的诗很好听”,也有苍老的墨痕:“年年登高,只为看一眼你看过的山”。这些朴素的话语,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能说明元稹在达州人心中的分量。
纪念馆的后院是“戛云小筑”,仿照元稹在通州的茅屋建造,竹篱围成的小院里,种着兰草和菊花——都是元稹诗里提到过的植物。茅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副简陋的木联:“身寄巴山客,心随楚水鸥”,是从他的《遣怀》中摘出的句子。屋内的木桌上,摊着未写完的诗稿,砚台里的墨汁仿佛还未干涸,墙角的陶罐里插着几支干枯的芦苇,让人想起他“芦苇为笔,大地为纸”的清贫岁月。有孩子跑进小院,指着桌上的毛笔问:“这是元九公用过的吗?”工作人员笑着答:“是呀,他正等着你来,教他写几句达州的新变化呢。”
3. 元九登高节:万人同赴的千年之约
对达州人来说,凤凰山的意义,一半藏在平日的晨钟暮鼓里,一半显在正月初九的“元九登高节”中。这场延续了近一千二百年的盛会,早已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9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
- 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章节目录,提供快穿系统:人人都为宿主着迷的最新更新章...
- 1784408字07-23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章节目录,提供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246299字07-24
-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
-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章节目录,提供[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606830字07-23
- 金手指是鲱鱼罐头汤[快穿]
- 金手指是鲱鱼罐头汤[快穿]章节目录,提供金手指是鲱鱼罐头汤[快穿]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215396字07-23
- 快穿:快跑!貌美白月光你惹不起
- 快穿:快跑!貌美白月光你惹不起章节目录,提供快穿:快跑!貌美白月光你惹不起的最...
- 1479935字0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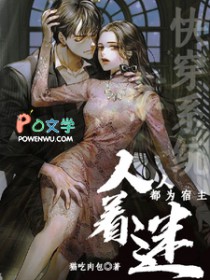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965/64965s.jpg)
![[综漫] 特级咒灵重力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281/64281s.jpg)
![金手指是鲱鱼罐头汤[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4/64407/64407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