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元稹: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
的水,能想起元九公的诗”。潭边的野菊开得正好,花瓣上的露珠滚落,像极了诗里没写完的韵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再往上走百余步,便是“相思树”——一棵三人合抱的黄葛树,树龄已逾百年。它的枝干虬曲苍劲,向四周伸展,像一双温柔的手臂拥抱着登山的人。当地人称它为“元稹与百姓的相思树”,因每年登高时,人们总爱在树枝上系红绸带,红绸带随风飘动,像无数条连接古今的思念。树皮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老人们说那是“元稹的诗行”,凑近细听,风穿过枝叶的沙沙声里,仿佛混着他当年吟哦的韵律。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把写有“愿爷爷健康”的绸带系在最低的枝丫上,她奶奶在一旁念叨:“元九公看着呢,会保佑咱的。”
半山腰的“碑林步道”,堪称“元稹诗廊”。百余块青石碑沿山路错落排列,每块碑上都刻着他在通州的诗作,字体或楷或隶,笔力或刚或柔,都是当地书法爱好者的手笔。从《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的“月照巴江客,猿声满翠微”,到《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的“地偏相识少,兵息侨寓多”,行至此处,仿佛在与诗人并肩登山。有穿校服的学生驻足在《离思五首·其四》的碑前,轻声念着“曾经沧海难为水”,同行的老师便趁机讲起元稹对亡妻的深情,说“好的文字,能让思念活上千年”。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碑上,字里行间仿佛有光斑跳动,像诗里藏着的星星。
最让人驻足的是“望河亭”。这是半山腰的一处木质凉亭,正对着蜿蜒的州河,元稹曾在此写下“州河如练绕山流,一带青烟锁画楼”。如今,亭内摆着石桌石凳,常有老人在此对弈、唱川剧。穿蓝布衫的老爷爷拉起二胡,调子是自编的《元九谣》,唱词里混着元稹的诗句:“元九公,住通州,戛云亭上望乡愁;州河水,慢慢流,载着诗情到永久……”琴声里,有个戴老花镜的老人正铺开宣纸,蘸着浓墨写“江碧鸟逾白”,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与二胡声、流水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活着的唐诗。
从望河亭再往上,山路渐陡,却更显幽静。路边的野草丛里,偶尔能看见野生的兰花,当地人说这是“元稹花”——相传元稹曾在山路旁种下兰花,说“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暗合自己虽被贬却不改初心的心境。如今,这些兰花年年春天绽放,淡紫色的花瓣上沾着晨露,像无数双凝视着山与河的眼睛。登山的人经过时,总会放慢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寂静,仿佛元稹就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小天师
- 小天师章节目录,提供小天师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3299018字07-22
- 终不负,凌云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顾榕)的经典小说:《终不负,凌云志》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742626字07-21
- 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巴蜀魔幻侠)的经典小说:《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最新章节...
- 1678967字07-21
- 穿白月光,攻美强惨[快穿]
- 1475120字07-19
- 朕当外室那些年
- 809304字07-19
- 穿成星际美食文炮灰
- 穿成星际美食文炮灰章节目录,提供穿成星际美食文炮灰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06058字0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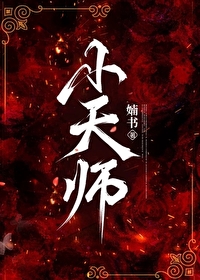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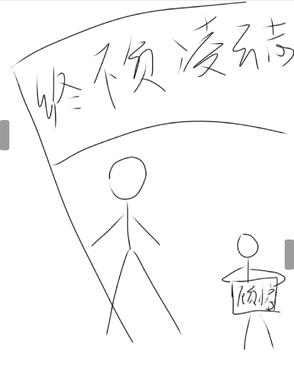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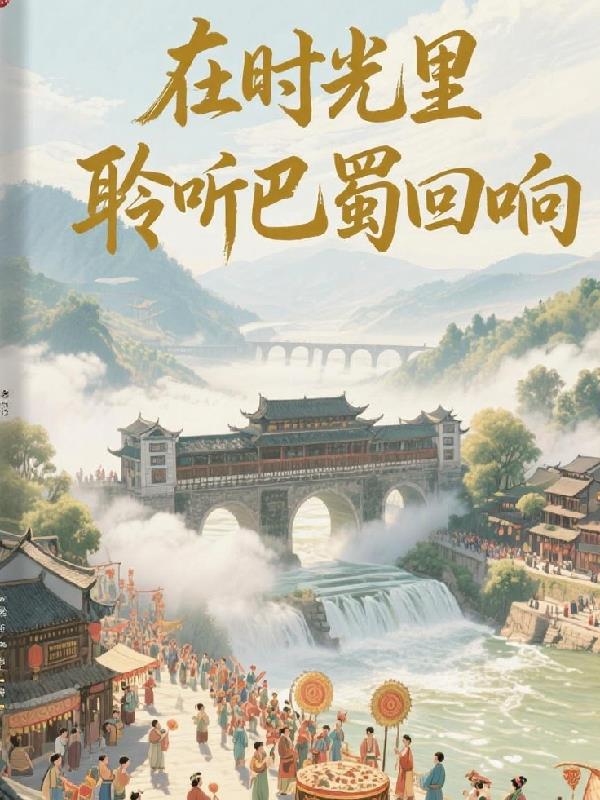
![穿白月光,攻美强惨[快穿]](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2/62771/62771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