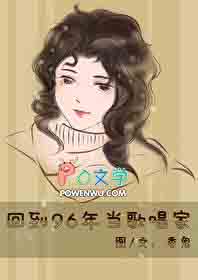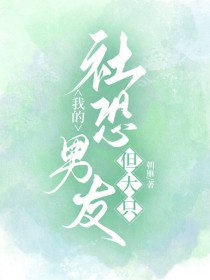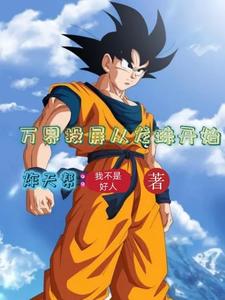第158章 钢与柔:成都东郊的双重叙事
夏后的暴雨总来得猝不及防。我撑着伞往东郊记忆走,远远看见老陈正把修车铺的工具往棚子里搬,铁皮棚被雨水打得噼啪响,倒像当年车间里的机床在合唱。"快来避避雨!"他朝我招手,递过条毛巾,"这雨跟1983年那场一样猛,当年厂里的排水沟都淹了,我们光着脚去疏通,王师傅的胶鞋被钉子扎破,血流在水里都看不见。"
雨停后,空气里飘着泥土和青草的混合味。演艺中心的屋檐下挂着水帘,几个穿工装的老人正指着墙面议论——那里隐约能看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被雨水泡得愈发清晰。"这墙跟人一样,老了就藏不住心事,"李大爷用手摸着砖缝,"当年刷标语时我站在梯子最上头,粉笔灰落了一脖子,现在脖子还痒呢。"
儿童乐园建在当年的托儿所旧址,滑梯是用废弃行车轨道改的,秋千架上缠着野蔷薇。有个扎冲天辫的小男孩正缠着王婆婆讲"会发光的管子",王婆婆从布包里掏出个玻璃弹珠,对着阳光举起来:"就像这样,蓝幽幽的,能照见你爷爷年轻时的模样。"男孩似懂非懂,把弹珠塞进裤兜,说要带去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看。
"老物件修复室"里,年轻人正给台老式刻线机上油。机器的铭牌已经模糊,但"红光电子管厂1972"的字样仍能辨认。"这是从废品站淘回来的,"负责人小林擦着手上的机油,"拆开时发现齿轮缝里卡着半张饭票,1987年的,上面还印着厂徽。"他说着拿出个玻璃罩,把饭票小心翼翼放进去,和刻线机摆在一起,像给时光做了个标本。
夜市开在当年的厂区主干道上,摊位的灯串映红了红砖墙。卖冰粉的姑娘用搪瓷碗盛粉,碗底印着"红光厂食堂";弹吉他的小伙唱着改编的《工人谣》,歌词里混着"车床示波管106信箱"的字眼。有个老人听得入神,跟着节奏轻拍大腿,膝盖上的旧工装裤磨出了毛边,却比任何潮牌都有分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在老邮局的旧址前遇见了李大姐的女儿,她现在是园区的档案管理员。"我妈总说,当年寄给106信箱的信,字里行间都带着劲,"她翻开一本泛黄的信札,"你看这封,1975年的,写'车间新到了苏联图纸,我要加班研究,不攻克技术难关不回家',多提气!"信纸边缘已经发脆,但字迹力透纸背,像刻在时光里的誓言。
秋分那天,园区办了场"厂服时装秀"。老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年轻人穿着印着厂徽的潮牌卫衣,一起走在由玻壳厂房改造的T台上。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2页 / 共13页
相关小说
- 被狗皇帝抄家后,我搬空了整个国库
- 3597231字04-25
- 回到96年当歌唱家
- 回到96年当歌唱家章节目录,提供回到96年当歌唱家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49356字07-23
- 漂亮炮灰已觉醒
- 174572字07-25
- 我的社恐男友,但大只
- 我的社恐男友,但大只章节目录,提供我的社恐男友,但大只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34920字07-26
- 万界投屏从龙珠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炸天帮:我不是好人)的经典小说:《万界投屏从龙珠开始》最新...
- 616504字11-08
- 彪悍农家女:我家灶台通90
- 1509194字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