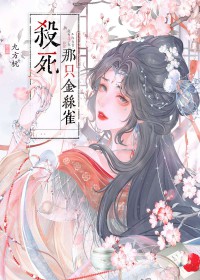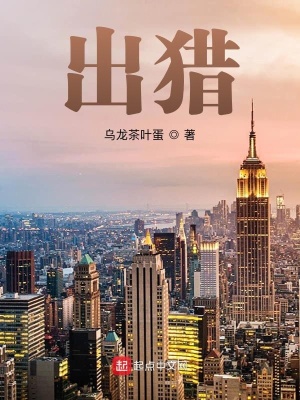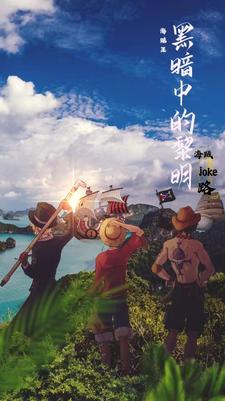第156章 成都庙会:旧时光里的民俗长卷
这铁家伙一天能织多少?抵得上十个婆娘吧!” 旁边的学堂展位更有意思,玻璃柜里摆着学生做的木船、泥偶,墙上贴满工整的毛笔字,先生站在高台上演说:“诸位乡亲,娃娃们得学新学问,才知这机器为啥会转!”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摇头,议论声混着机器声,像锅熬得正香的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跟着父亲来赶过一次,他想买个新竹筐装菜籽。走到竹篾摊前,摊主正埋头编筐,篾条在他手里听话得很,左绕右穿就成了花纹。“要多大的?” 摊主头也不抬,手指翻飞。“能装两斗菜籽的。” 父亲蹲下来,捏了捏筐沿的篾条,“这篾够韧不?” 摊主停下活计,拿起竹筐往地上一摔,“您瞧,裂了算我的!” 俩人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父亲付了钱,摊主又多塞了个竹编的小簸箕:“给娃装零嘴,算添头。” 我捧着小簸箕,瞅见隔壁糖画摊在画《三国》人物,赶紧拽着父亲的衣角,他笑着给了两个铜板,糖画师傅舀起糖稀,手腕一转,一条鳞爪分明的小龙就卧在了竹板上,凉透了咬一口,甜得舌尖发麻。
会期快结束时的评比最是热闹。得奖的商户披红挂彩,捧着银质的奖牌站在台上,那奖牌上刻着“优选”二字,阳光照得晃眼。卖豆瓣酱的王掌柜那年得了奖,回来就把奖牌嵌在柜台里,说要“让酱菜都沾沾光”。果然,他的豆瓣酱涨价一分,买的人反倒排起队,有个老主顾说:“吃他的酱菜,就像吃着成都的体面。”
(六)打金章与江湖艺
青羊宫花会的热闹里,藏着股阳刚气——那是“打金章”的擂台在叫阵。三丈见方的木台用粗麻绳捆在石柱上,红绸子缠在台柱顶,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在给好汉们加油。台口挂着“以武会友”的匾额,黑底金字,被太阳晒得发亮。从1918年起,每年庙会都要摆上半月,先是各码头的武师比拳脚,最后胜出的能得枚纯金的奖章,那“金章”在成都武林的分量,比元宝还重。
我挤在台边的人群里,踮着脚才能看见台上。正赶上两个汉子较量:穿黑短褂的是练查拳的,矮壮结实,脚步轻快得像踩在棉花上;穿白汗衫的高个练洪拳,胳膊上的腱子肉鼓鼓的,拳头挥起来带风。俩人先是抱拳行礼,“请指教”三个字刚落,黑褂师傅就一个垫步冲拳,拳头擦着白汗衫的耳边过去,带起的风扫得台边的观众直缩脖子。白汗衫师傅侧身躲过,反手一掌劈向对方腰眼,黑褂师傅弯腰避开,顺势一个扫堂腿,白汗衫踉跄着后退两步,台下顿时爆发出“好!”的喝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17页
相关小说
- 七零之攀高枝
- 2932411字07-29
- 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
- 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章节目录,提供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的最新更新章节列...
- 1096369字07-26
- 出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乌龙茶叶蛋)的经典小说:《出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588859字07-27
- 【海贼王】黑暗中的黎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贼joker路)的经典小说:《【海贼王】黑暗中的黎明》最新章...
- 883560字07-29
- 我的后院通废土
- 1242876字07-30
- 斗罗2:这个龙神武德过于充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台首座下小野猪)的经典小说:《斗罗2:这个龙神武德过于充沛...
- 1505974字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