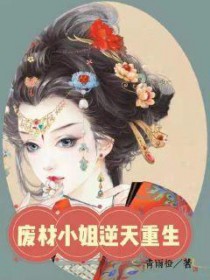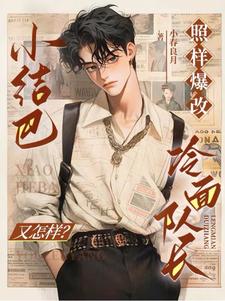第147章 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宦海沉浮的辗转
黄州之后,苏轼的贬谪之路仍在继续。从汝州到惠州,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每一次迁徙,都是对身心的巨大考验。在惠州,他本想安度余生,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洒脱诗句,却因一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被政敌曲解为过于惬意,再度被贬至更远的儋州。
然而,无论身处何地,苏轼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官的初心。在杭州,他见西湖湖面淤塞,葑草蔓生,便主持疏浚工程。他亲自勘察地形,制定方案,发动民众清理湖底淤泥,将挖出的泥土筑起一道长堤。这道后来被称为“苏堤”的长堤,不仅改善了西湖的生态环境,更为百姓提供了一处赏景休闲的好去处。在颍州,他治理水患,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确保农田免受洪水之灾。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与担当。
黄州涅盘:在困境中自我蜕变
定慧院中的孤寂
初到黄州,苏轼暂住在定慧院的一间小屋内。这间屋子破旧不堪,墙壁上布满了裂痕,屋顶的瓦片也有多处破损,每逢雨天,便会滴滴答答地漏雨。屋内潮湿阴暗,蛛网遍布,散发着一股霉味。唯有窗外那轮缺月和几株疏桐,成为了他寂寥生活中的陪伴。
深夜,万籁俱寂,苏轼常常难以入眠。他披上外衣,在院中徘徊。月光洒在地上,清冷而孤寂,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随着脚步在地面上晃动。此时,他的心中满是迷茫与失落,于是,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他的笔下流淌而出:“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词中的“孤鸿”,正是他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孤独、迷茫,却又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东坡田亩的耕耘
好友马梦德见苏轼生活窘迫,便为他向官府求得城东的一块荒地。这块地杂草丛生,石块遍布,开垦起来极为困难。但苏轼没有丝毫抱怨,他亲自扛起锄头,日复一日地劳作。春日里,他翻耕土地,播种稻种,汗水湿透了衣衫,泥土沾满了裤腿;夏日里,他顶着烈日除草、施肥,皮肤被晒得黝黑,双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他将这片荒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在田间劳作的日子里,他深刻体会到了稼穑之苦,也收获了劳动带来的快乐。“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这句诗记录了他开荒的艰辛;而“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16页
相关小说
- 逆天重生:废物七小姐
- 逆天重生:废物七小姐章节目录,提供逆天重生:废物七小姐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716378字07-17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快穿:在甜文里被大佬们亲哭
- 2379868字05-19
- 御魂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魂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4766625字07-29
- 乃木坂之打工少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喵森葵)的经典小说:《乃木坂之打工少女》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41465字12-24
- 小结巴失忆后,被高冷队长宠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春良月)的经典小说:《小结巴失忆后,被高冷队长宠翻了》最...
- 578127字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