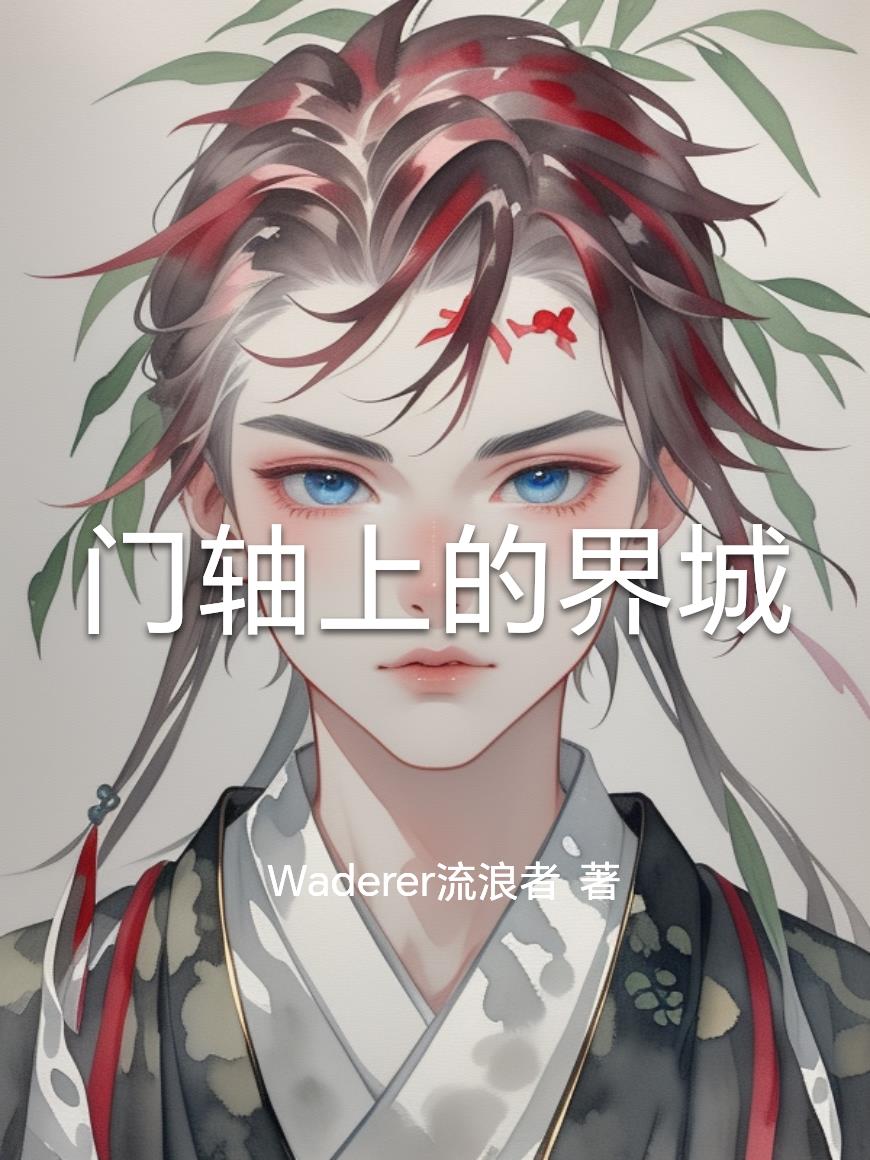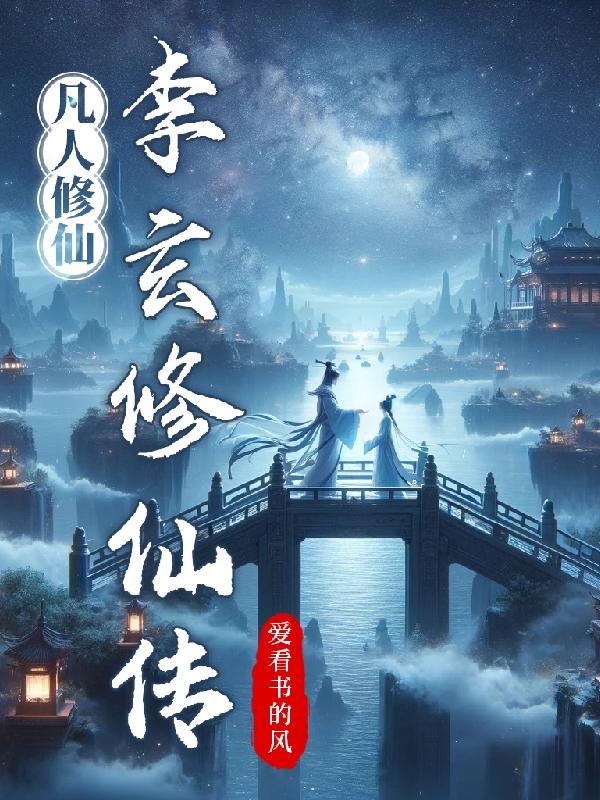第129章 化解工厂与村民的矛盾(下)
八月的烈日炙烤着工地,搅拌机的轰鸣声中夹杂着蝉鸣,我抱着图纸站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前,望着聚集在警戒线外的村民,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
三天前,因木粉飞扬引发的争执还历历在目,此刻他们紧锁的眉头和交叉的双臂,仍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们之间。
“各位叔婶,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说说我们整改的新方案。”
我展开图纸铺在长条桌上,图纸边缘被晒得微微卷起。指尖划过标注着隔音墙的平面图,“这堵隔音墙高四米,用空心砖加吸音棉,既能挡住木粉,又能降低切割噪音。”
人群中有人伸长脖子凑近细看,李大爷拄着拐杖往前挪了两步,浑浊的眼睛盯着图纸上的线条。
说到木粉处理环节时,我调出手机里的照片:“我们打算在仓库安装脉冲除尘器,收集的木粉会定期运到生物质燃料厂。”
话音未落,王婶突然开口:“说得好听,上次不也说盖防尘网?结果风一吹全散了!” 她身旁几个村民跟着点头,现场气氛瞬间紧绷。
我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掏出检测报告:“这是第三方机构的数据,除尘器效率能达到 98%。而且我们准备雇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负责日常清理,既能解决就业,也方便大家监督。”
人群中响起细碎的议论声,张大哥挠着头说:“要是真能在家门口挣钱,倒也不是不行。”
随着讨论深入,气氛渐渐缓和。我把带来的笔记本摊开:“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咱们一起想办法。”
李大爷用拐杖轻点地面:“要是下雨天,木粉堆会不会被冲进排水沟?” 这个问题让我眼前一亮,赶紧记录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建议,从排水沟改造到运输路线规划,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夕阳把工棚的影子拉得很长时,原本剑拔弩张的村民们,竟围坐在一起讨论起木粉回收的细节。
这场风波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深夜的办公室里,台灯下摊满了《工业粉尘治理技术》《循环经济案例集》,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各类环保设备的参数。
我频繁往返于图书馆和建材市场,向设计院的老工程师请教除尘系统设计,甚至跑到邻市的木材加工厂实地考察。
那些日子,手机里存满了与专家的通话录音,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方案草图。
白天的走访同样艰辛。记得第一次敲开王婶家的门,她隔着防盗门打量我:“又来做工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门轴上的界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Waderer流浪者)的经典小说:《门轴上的界城》最新章节全文阅...
- 701995字07-21
- 猎魔人:基里曼大师拒绝女术士
- 1351279字07-21
- 证道,别人成神,我成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发呆富贵)的经典小说:《证道,别人成神,我成仙》最新章节全...
- 529471字07-21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孤臣血,玄启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用户19910905)的经典小说:《孤臣血,玄启燃》最新章节全文阅...
- 859183字07-21
- 凡人修仙,李玄修仙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看书的风)的经典小说:《凡人修仙,李玄修仙传》最新章节全...
- 760762字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