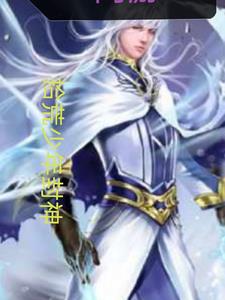第2427章 钢笔尖的永恒坐标
艺术节的余温还未散去,钢笔书法展继续在图书馆举行。新增的“国际展区”里,外国友人用中文写下的“正义”二字,笔迹里隐约能看到父亲的影子。“这是‘笔迹传染’。”赵峰笑着说,他刚从云南的钢笔工厂回来,眉骨的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浅红,“我们教外国工匠刻‘之’字标记,现在全世界的正义使者,都在用和你父亲相似的钢笔。”
他递过来支钢笔,笔杆上刻着串复杂的坐标,末端是个小小的向日葵。“这是用1987年那批赈灾款的剩余资金做的,全球限量发行三千七百支,每支的坐标都不一样,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有需要的地方。”赵峰指向地图,“已经有八百支漂到了战乱地区,当地的孩子说,要像希望小学的学生一样,用钢笔写下和平的愿望。”
母亲的视频通话带来了云南的消息。女老师站在新落成的“国际交流中心”前,身后的孩子们举着与外国小朋友的合影,照片里的钢笔上都有“之”字标记。“小向日葵的妹妹收到了非洲孩子的回信,”母亲的声音带着笑意,“信里说,他们学会了用钢笔写‘希望’,还在教室后面种了向日葵,说要朝着中国的方向开花。”
傍晚的地理园格外安静,夕阳给石碑镀上了层金边。林砚之打开直播,镜头对着那支全球限量版钢笔,屏幕上涌入世界各地的留言:“我在叙利亚收到了钢笔!”“巴西的孩子们用它写环保倡议书!”“德国的法治课上,我们在学1987年的案子!”每条留言后面,都跟着个向日葵表情。
闭园前,林砚之在“世界池塘”里放下了最后一艘模型船。船上的钢笔刻着希望小学的坐标,笔帽里藏着张纸条:“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你握住这支笔,就离正义近了一步。”船缓缓漂向中心时,她忽然明白父亲那句话的深意——正义从不是孤立的坐标,是无数个点连成的线,能绕地球一圈,也能回到最初的起点。
赵峰推着老陈走来,老人的手里举着新的星图。“你看,”老陈指着猎户座的腰带星,“这三颗星的连线延长线,正好指向希望小学的坐标。你父亲当年没说瞎话,正义真的有轨迹。”星图的角落,贴着张孩子们画的画,地球被钢笔圈起来,旁边写着“我们的坐标,也是世界的坐标”。
夜色渐浓,地理园的灯光次第亮起,照亮了那些散布的钢笔模型。林砚之站在地球仪前,看着那道连接希望小学与云南的金线,忽然觉得它像根无形的钢笔,正在世界的版图上书写新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头,永远是1987年那个雨夜,父亲握着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御鬼者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沙之愚者)的经典小说:《御鬼者传奇》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3193750字06-25
- 穿呀主神
- 9313930字07-30
- 我一个刺客全点防御属性很合理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枫小尘)的经典小说:《我一个刺客全点防御属性很合理吧》最...
- 3095427字09-12
- 末世重生,见识到不一样的末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春风得意醉不归)的经典小说:《末世重生,见识到不一样的末世...
- 561791字09-12
- 网游:拾荒少年封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夜无忧伤)的经典小说:《网游:拾荒少年封神》最新章节全文...
- 3096351字07-29
- 重生在电影的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盏茶煮酒)的经典小说:《重生在电影的世界》最新章节全文阅...
- 7893277字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