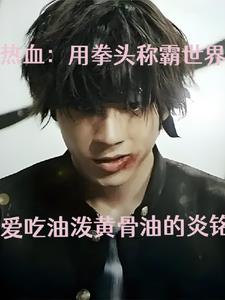第352章 烛留一线暖深宵
紫檀木筒中那幅墨痕浓重、承载着北境万里河山与挚友滚烫誓言的《边图》,被澈儿以最郑重的姿态,悬于东宫书房内室最醒目的位置。羊皮卷轴展开,沈骁刀刻斧凿般的“山河万里,待君共守”六字,如同燃烧的烙印,日夜灼烫着他的心魄。北境的朔风、边关的冷月、金戈铁马的呼啸,仿佛透过这图卷,化作无形的战鼓,擂响在耳畔,催促着他加快步伐,廓清宇内,以不负这重托,不负那“共守”之约。
然而,“共守”非一蹴而就。欲定边关,先安内政。律法,乃国之重器,安民之基,更是吏治清明、新政推行的根本保障。大靖立国数十载,律法条文叠床架屋,繁冗晦涩,且多承袭前朝旧制,其中不乏不合时宜、互相抵牾、乃至被胥吏曲解盘剥、成为压榨小民工具的恶法旧规。澈儿深知,欲固国本,必先正律法。
东宫书房的灯火,自此燃得比以往更久、更亮。宽大的紫檀书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被暂时挪至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厚厚数摞泛黄发脆的《大靖律疏》原本、历代刑部案卷汇编、以及各地呈报的律法疑难与民间诉讼实例。
澈儿埋首其间,如同最勤勉的矿工,在浩瀚而芜杂的律法矿脉中艰难掘进。他时而凝神细读律条原文,眉头紧锁,朱笔在晦涩古奥的字句旁批注质疑;时而翻阅积年案卷,目光锐利如刀,剖析判决是否公允,律条适用是否得当;时而又对着各地呈报的疑难卷宗陷入沉思,推敲律法与人情、法理与现实的微妙平衡。
窗外,夜色深沉如墨。秋风掠过庭院,卷起落叶,发出沙沙的轻响。书房内,烛火通明,映照着澈儿伏案的身影。他换下了储君常服,只着一件素色的细麻直裰,袖口沾染了点点墨迹。腰后那方靛青色的药草暖垫散发着温润的清苦,无声地支撑着他挺直的腰脊。然而,连续数日的高强度钻研,心神如同绷紧的弓弦,体力的消耗亦是巨大。
此刻,他正面对着一份关于修订《户婚律》中“田宅典卖”条款的草案。此条款关乎万千小民身家性命,旧律繁复晦涩,典权、找贴、回赎等环节极易被豪强和胥吏利用,巧立名目,侵吞民产。澈儿苦思良久,试图在保障交易安全与杜绝盘剥之间找到最精炼、最清晰的平衡点。他反复推敲着草案上的每一个字眼,删去冗余的限定词,合并重复的条款,力求用最简洁直白的语言,表达最严谨的法意。
烛泪无声地堆叠在黄铜烛台上,凝成厚重的琥珀色小山。夜渐深,万籁俱寂。案头那盏最大的烛台,火光跳跃,将澈儿专注的侧影投在身后的书架上,随着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迟暮流年)的经典小说:《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最新章节全...
- 4147110字04-17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你透视眼不去赌石,乱看什么呢!
- 【小人物逆袭+透视+赌石+鉴宝+捡漏+神豪】秦朝阳,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社会晃荡两年...
- 3795767字10-02
- 重回80:全村把我当财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牡丹一度)的经典小说:《重回80:全村把我当财神》最新章节...
- 4428604字12-17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
- 热血:用拳头称霸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油泼黄骨鱼的炎铭)的经典小说:《热血:用拳头称霸世界...
- 711248字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