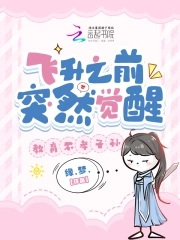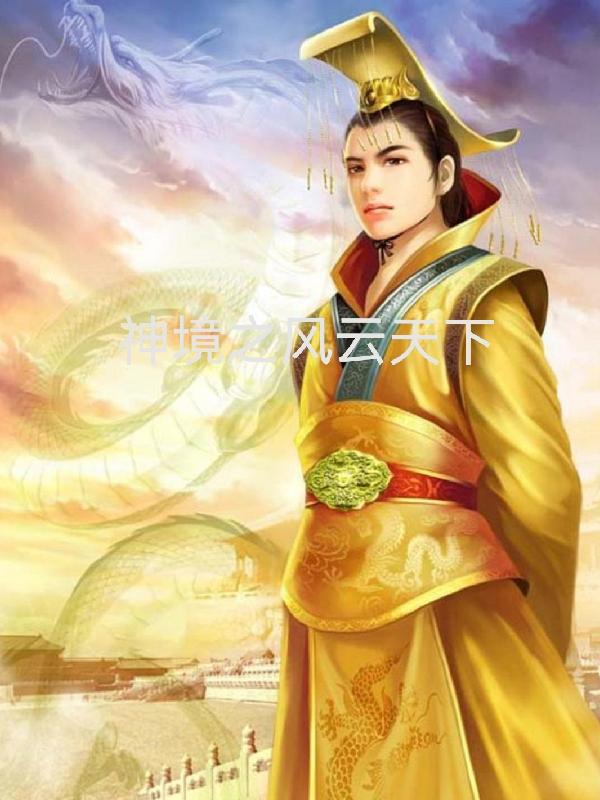第105章 墨匠云集,技术飞跃
幽州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却吹不散蓟城工坊区蒸腾的热浪与人心里的那份滚烫。刘虞兑现了他的承诺,在蓟城西北角划出了一片戒备森严的区域,依托原有的官坊基础,一座规模远超冀州时期、设施更为完备的“幽州格物院”拔地而起。高耸的烟囱日夜不息地喷吐着黑烟,铁砧的敲击声、锯木的嘶鸣、水车的轰鸣汇聚成一股磅礴的工业交响,这里是刘辩意志延伸的熔炉,是他撬动时代的支点。吸引北地工匠的榜文早已发往各郡,开出的条件优厚得令人咋舌:高于市价数倍的薪酬、专供匠户的良田宅院、子女可入新式蒙学、技艺卓绝者甚至能得“格物博士”头衔,享士人待遇。重赏之下,加上刘虞这位仁厚州牧的背书,幽州乃至更北边塞的能工巧匠们如同百川归海,源源不断地涌向蓟城。他们中有世代打铁的冶户,有精于营造的木石大匠,有专攻弓弩的军器匠人,甚至还有几个操着古怪口音、据说祖上是前朝将作大匠的后裔。工坊的规模急剧膨胀,各类分工明确的车间建立起来,冶炼、锻造、木工、皮革、弓弩、器械……空气里弥漫着焦炭、铁腥、桐油和汗水的混合气息,秩序中透着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然而,真正让刘辩心跳加速的,是夹杂在普通工匠中,那几支气质迥异的队伍。他们人数不多,衣着简朴甚至有些破旧,神情却异常沉静专注,眼神锐利如鹰隼,随身携带的工具箱也与众不同,里面是各种奇形怪状、打磨得异常精密的青铜或铁质构件、规、矩、绳、水准仪,还有一些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用途的器物。领头的是几位须发皆白或正值壮年的汉子,他们自称来自辽东或代郡的山野,言语间带着古意,对官府的登记盘问显得疏离而警惕。刘辩亲自接见了他们,当其中一位最年长的老者,在戒备森严的密室中,从怀中取出一枚非金非木、刻着复杂几何纹路和“兼爱”、“非攻”古篆的令牌时,刘辩心中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墨家!这些自称“山野匠人”的,正是传承了数百年、早已隐没于历史尘埃的墨家机关术后裔!老者名叫墨桓,是这支北地墨者的首领。他们并非响应榜文而来,而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最初是冀州流传出的改良水车、高效农具的图纸,其设计思路暗合墨家“节用”、“兴利”的宗旨;后来是界桥之战中,刘虞军使用的威力惊人的“炮”(投石机)和传闻中能连发数矢的弩机,其精巧的杠杆、滑轮、齿轮运用,更是让这些墨者寝食难安。墨家讲究“实学”、“巧技”,对能推动“天下之利”的技艺有着近乎本能的追求。当打探到这些技术的源头竟在幽州,且与一位名叫“刘兴”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魔王大人,勇者他又招了
- 909747字07-13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
- 我就是个反派,你们倒贴做什么?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东方梦梦)的经典小说:《我就是个反派,你们倒贴做什么?》最...
- 524099字09-15
- 九幽剑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剑言)的经典小说:《九幽剑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3045836字03-07
- 飞升之前突然觉醒,教育不孝子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梦.)的经典小说:《飞升之前突然觉醒,教育不孝子孙》最新...
- 587875字12-25
- 神境之风云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笑傲天地)的经典小说:《神境之风云天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2282363字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