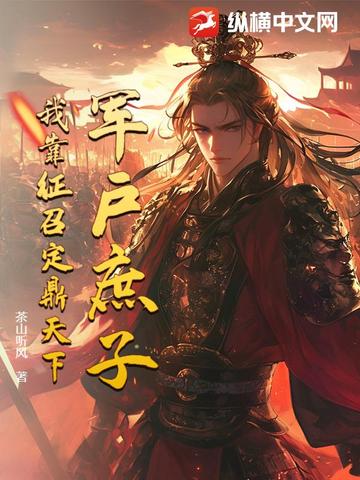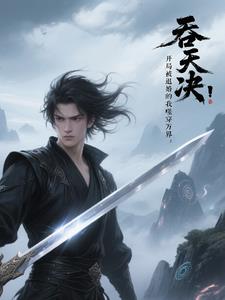第351章 河口三角洲与泥沙迷局
本裸露的滩涂正被缓慢淹没,红树林的树干上,去年的潮水痕迹此刻已没入水中,“这种河口的潮汐比外海晚一个时辰,涨起来慢,退下去也慢,就像个没睡醒的懒汉,可一旦发力,能把船推上滩涂。” 他让人将长绳系在红树林的气根上,借助树木的拉力稳定船身,绳结处的气根虽然纤细,却异常坚韧,能承受整艘船的拖拽力。
船员们在一处相对开阔的水域发现了惊喜。红树林的间隙中隐藏着一条天然水道,水深丈许,水流清澈,与周围的浊水形成鲜明对比。水道两侧的泥滩上,布满了螃蟹的洞穴,洞口堆积着圆形的泥球,如同被精心雕琢的珠子。几只白鹭站在泥球上,细长的喙精准地啄向洞穴,每一次都能叼出一只挣扎的螃蟹,动作娴熟得如同技艺精湛的工匠。
“跟着白鹭走!” 渔民出身的船员指着水道深处,“这种鸟专挑干净的水道落脚,底下的泥硬,没那么多烂泥田,而且它们知道哪有鱼,跟着准能找到出海口。” 他说得没错,当船队顺着白鹭的飞行轨迹航行时,测深绳显示的水深始终稳定,船底再未出现擦过泥沙的声响,红树林的气根也渐渐稀疏,水道愈发宽阔。
河口的泥沙中隐藏着另一重宝藏。船员们在清理船底的淤泥时,发现泥块中混着细小的陶片,胎质细腻,表面还残留着青色的釉彩,显然是古代瓷器的碎片。更令人惊喜的是,一片较大的陶片上,竟能辨认出 “越窑” 的字样,边缘的莲纹图案与泉州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瓷器如出一辙,说明此处曾有繁荣的航运活动,只是被泥沙掩埋在岁月深处。
“是泥沙把古城藏起来了。” 宝儿抚摸着陶片上的纹路,边缘的磨损显示它已在水中浸泡了数百年,“大河每年带来的泥沙能堆出半尺厚的新土地,年深日久,连城池都会被埋进地下,就像被大地收进了仓库。” 她让人将收集到的陶片编号记录,与灰岩岛发现的 “永乐三年” 标记对比,发现两者的纹饰风格有传承之处,显然是同一区域不同时代的人类活动痕迹。
夜幕降临时,河口的水面泛起微弱的磷光,与灰岩岛的发光贝类不同,这是淡水与咸水交汇时,微生物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光芒,如同散落的萤火虫在水中游动。这些光点并不固定,而是随着水流的分层上下浮动,上层淡水区的光点稀疏,下层咸水区的光点密集,恰似天然的指示灯,标记着水域的深浅。
“这些光是最好的水深表。” 宝儿指着光点密集的区域,“咸水区的泥沙少,水深足够;光点稀的地方是淡水带来的泥沙淤积,船底容易搁浅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本来只想带崽,结果全师门都跟我混
- 284359字07-23
- 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茶山听风)的经典小说:《军户庶子,我靠征召定鼎天下》最新章...
- 611379字07-26
- 霸天武魂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千里牧尘)的经典小说:《霸天武魂》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1329324字07-26
- 功德金仙,从斩奸除恶开始
- 3560242字11-08
- 血炼妖帝
- 2663288字07-25
- 吞天诀:开局被退婚的我噬穿万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简羽)的经典小说:《吞天诀:开局被退婚的我噬穿万界》最新...
- 711321字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