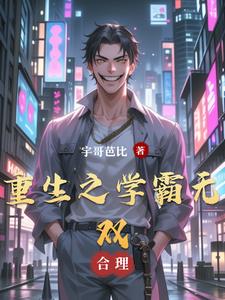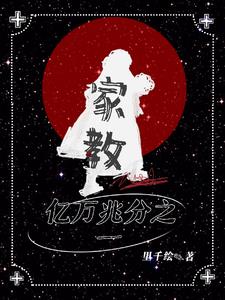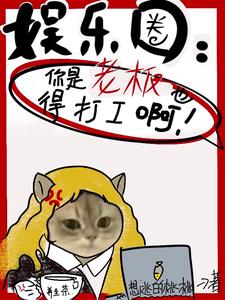第122章 饥荒
做犁耙,树枝当柴烧,树根留着明年再种。"
全民总动员开始了。妇女们带着竹篓上山,挖野薯、摘野莓、剥棕榈芯;男人们拆了自家的篱笆当柴火,把腌菜坛里的酸笋全倒进大锅;孩子们捡来晒干的玉米芯,在晒谷场搭起"临时粮仓"。陈耀带着合成团的士兵,开着推土机平整出二十亩新地,从邻国买来旱稻种子——这是他用十车榴莲干跟老挝农民换的。
"陈叔,"阿依抱着小棠站在田埂上,手里举着个搪瓷缸,"学校停课了,孩子们说要来帮忙插秧。"她晃了晃缸子,"这是我攒的鸡蛋,给工地上的叔叔阿姨补身子。"
陈耀接过缸子,摸了摸小棠的头。这孩子最近总跟着医疗组跑,学会了认草药,此刻手腕上还系着他送的红绳。"告诉孩子们,"他说,"等稻子抽穗了,每人分两穗,留着当种子。"
经济制裁的压力越来越大。洪兴的橡胶园被列入"非法资产",国际买家纷纷撤单;银行账户被冻结,连士兵的津贴都发不出。但最让陈耀揪心的,是村东头的老阿公——他藏着半袋米,说要留给即将生产的儿媳,自己啃了三天树皮,现在躺在草屋里,嘴唇裂得渗血。
"陈先生,"阿凯蹲在草屋门口,"老阿公不让动他的米。他说,'我活了七十岁,没见过当官的跟老百姓同吃树皮。'"
陈耀沉默了。他走进草屋,老阿公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米袋,米袋上还缝着红布——是他孙女的百家衣。"大爷,"陈耀蹲下来,"我是陈耀,洪兴的陈叔。"
老阿公抬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陈...陈先生?"他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本子,"我儿子在金象帮当马仔时,您给他治过腿伤。他说您说过,'洪兴的地盘,饿不死人'。"
陈耀接过本子,上面歪歪扭扭记着:"民国三十八年,陈先生带医疗队来,给我娘治疟疾,没要一分钱。"
"大爷,"陈耀把米袋塞回他怀里,"您把这米熬粥,给儿媳补身子。米不够,我让人送红薯来。"他指了指窗外,"您看,后山的葛根都挖完了,河里的鱼也捞干净了——可咱们的地在,人在,就能再种出粮食。"
转机出现在九月的雨夜。中国农机厂的货轮绕道菲律宾,悄悄停靠在缅北边境码头。船舱里装着五十台拖拉机、二十台播种机,还有两百吨杂交稻种。随船来的技术员老张拍着陈耀的肩:"陈总,我们厂长说,'洪兴的人能让榴莲树改种橡胶,能让毒贩的地变成稻田,这样的政府,该帮。'"
本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靡靡之音(H)
- 快穿之靡靡之音(H)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快穿之靡靡之音(H)》情节跌宕起伏、扣...
- 494579字12-13
- 重生之学霸无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宇哥芭比)的经典小说:《重生之学霸无双》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183994字12-15
- 她不可妻
- 她不可妻章节目录,提供她不可妻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14796字09-28
- 家教:亿万兆分之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里千绘)的经典小说:《家教:亿万兆分之一》最新章节全文阅...
- 599905字10-04
- 拐个巨星谈恋爱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想逃的桃桃)的经典小说:《拐个巨星谈恋爱》最新章节全文阅...
- 1669634字12-24
- 靠假揣崽在暴君手下苟活
- 571158字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