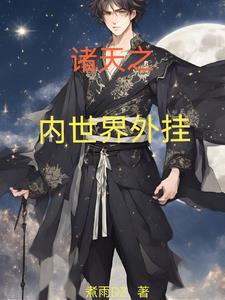第125章 胡风汉韵汇许都,开放包容气象新
出精细的凹凸纹饰。中原工匠擅长铸造和镶嵌,对这种更依赖手工、能表现更细腻层次的技法颇感新奇,纷纷拿起工具尝试。
“此技用于金银器装饰,定能增色不少!”一位专攻首饰制作的工匠兴奋地说,“以往我们多用模铸或累丝(金银丝编织),精细处总觉不够灵动。此法可补其不足!”
与此同时,在户部一间宽敞的值房内,气氛则显得更为严肃。几位精通算学的官员和来自天竺的学者婆罗门正围坐在一起。桌案上,摊开着几卷用梵文书写的算学典籍,以及中原的《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婆罗门学者指着典籍上那些奇特的符号(0, 1, 2, 3, 4, 5, 6, 7, 8, 9),耐心地向汉官们解释着这种源自天竺的“位值制记数法”。
“请看,”婆罗门用羽毛笔在纸上写下“123”,然后用生涩的汉语解释,“此‘1’,代表一百;‘2’,代表二十;‘3’,代表三。位置不同,意义不同。此‘0’,代表空位,不可或缺。”他又写下“102”,强调道:“若无此‘0’,则易与‘12’混淆。”
他又演示了用这种符号进行加减乘除运算,步骤清晰,书写简便,远胜于中原传统的算筹摆弄或繁琐的汉字数字记录。负责国库钱粮核算的户部侍郎看得连连点头,眼中异彩连连:“妙!妙啊!此法用于登记田亩赋税、核算库银出入、计算工程物料,效率何止倍增!省却多少摆弄算筹、誊抄数字之苦!”他立刻意识到这套符号系统对于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巨大价值。
一位年轻的算学博士则更关注天竺典籍中记载的几何知识和三角测量方法,这些方法在土地丈量、水利工程和天文观测中有着潜在的应用前景。他与婆罗门学者就一个关于圆面积计算的公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双方在纸上写写画画,虽然语言沟通需要通译协助,但数学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共通的。
夕阳的余晖再次洒满许昌城,将这座融合了古老与新生、本土与异域的都城染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忙碌了一天的老赵头,难得清闲,踱步到城南一处新开的胡人酒肆前。酒肆里传来欢快的龟兹乐曲,节奏鲜明,鼓点铿锵。他驻足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平和的笑容。酒肆门口,几个刚下值的年轻工匠,正学着胡人的样子,就着喷香的胡麻饼,小口啜饮着琥珀色的蒲萄酒,脸上洋溢着轻松与好奇。
老赵头没有进去,只是站在街角,望着眼前这幅生动和谐的画面:汉装的士子与裹着头巾的胡商并肩而行,讨论着某件新奇的货物;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