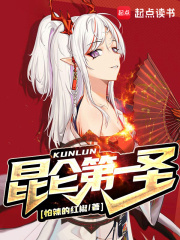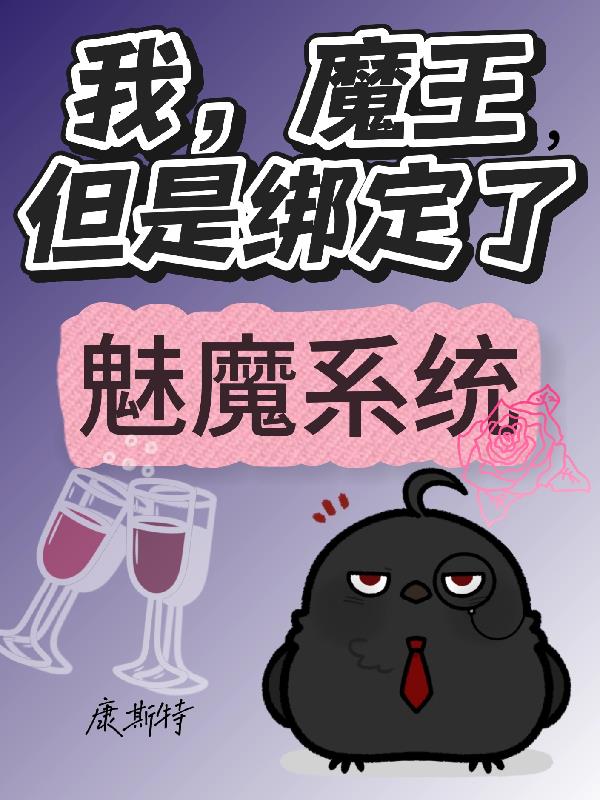第85章 马钧遣匠施暗手,轴承崩坏粮运瘫
里面是粘稠如墨、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膏状物。“此为‘蚀骨膏’,乃以强酸(注:此处可理解为当时可能存在的天然强酸物质如绿矾油等,或马钧通过特殊矿物提炼的腐蚀性液体)混合油脂、硫磺秘制而成。其性阴毒,涂抹于轴承滚道及齿轮啮合之处,初时无异状,然日积月累,与运转摩擦产生的微热相激,便会缓慢蚀铁,使其强度骤降,如同朽木。”
鲁三看着那罐黑膏,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这已非寻常破坏,而是针对器物命脉的、精准而阴狠的“绝杀”。
“此二法,一为‘内损’,一为‘外蚀’。”马钧将仿制轴承和蚀骨膏推向鲁三,“汝等此行,便是要将这些‘特制’的轴承,神不知鬼不觉地替换掉蜀军,尤其是刘备军运输队中那些关键位置木牛流马上的原装轴承。同时,伺机在刘璋军,甚至刘备军后方工坊的备用轴承或待装齿轮上,涂抹此膏。”
他目光如炬,紧盯着鲁三:“蜀地工坊初兴,管理必有疏漏。汝等皆是我亲手调教,精于机巧,伪装身份混入其工匠之中,或扮作行商接近其工料采买之人,并非难事。切记,只换关键承重部位之轴承,涂抹亦需隐蔽,万不可贪多求快,引人疑窦。待其大批量投入前线重载运输,便是隐患爆发之时!”
“小人…小人明白!”鲁三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将轴承和陶罐收入一个特制的、内衬软木防震的藤箱中,“定不负大人所托!”
“此行凶险,务必谨慎。”马钧最后叮嘱道,“刘基主公之意,非为杀伤,而在‘迟滞’。让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在关键时刻,变成压垮刘备蜀地根基的最后一根稻草。”
蜀地,葭萌关以西,金牛道
秋意渐浓,山风已带寒意。蜿蜒的金牛道上,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伍正艰难前行。数百架“木牛流马”在士卒和民夫的推拉下,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满载着前线刘备大军急需的粮秣、箭矢和修补军械的铁料。负责押运的偏将王平,眉头紧锁,望着前方望不到头的山路和阴沉的天色,心中莫名地有些烦躁。
“将军,这新造的‘木牛’是好使,省了不少人力,可这路…也太难走了。”一名什长抹了把汗,抱怨道。
王平没有答话。他何尝不知蜀道难?诸葛亮军师发明的这木牛流马,已是大大缓解了运力。但前线的消耗如同无底洞,尤其是黄忠将军镇守葭萌关,直面张鲁压力,魏延将军奇袭江州后,更是需要大量物资巩固防线、震慑刘璋。这次运输的物资,关乎未来一个月的军需,不容有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昆仑第一圣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怕辣的红椒)的经典小说:《昆仑第一圣》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862430字07-13
- 我,魔王,但是绑定了魅魔系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康斯特)的经典小说:《我,魔王,但是绑定了魅魔系统》最新章...
- 402517字07-15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
- 至尊剑帝
- 叶家世子叶青,为家族而战,却被剥夺血脉,关押天牢,九死一生。为了生存,叶青屠尽一切...
- 17785183字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