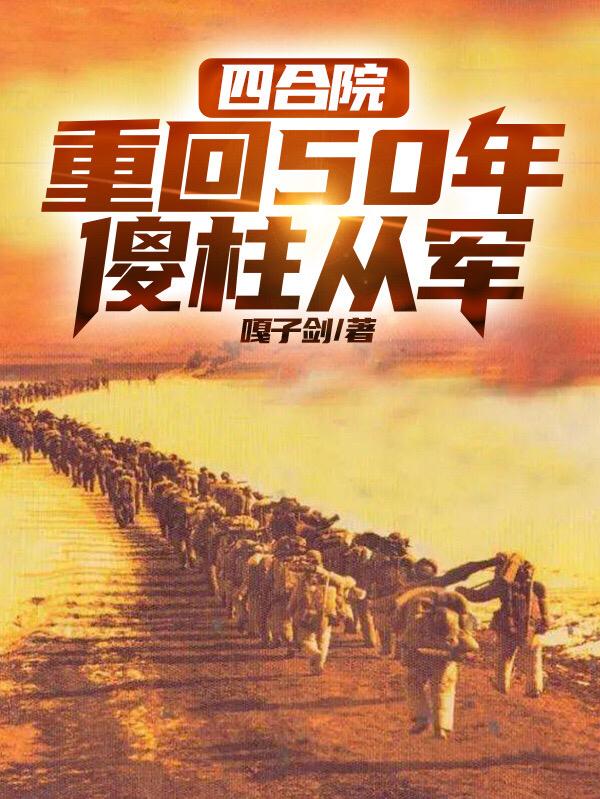第197章 墨水渗透与陶土吸水的物质交换实验
“陶土不喜欢太精确的东西。”她把那小块陶土揉成扁圆,像片微缩的土地,“你看,它刚才吸了我掌心的汗,边缘已经比中心硬一点了。”
他果然看见土坯边缘泛着浅灰,像被时光提前风干的痕迹。这让他想起上周去考察的老教堂,石墙上的斑驳水痕也是如此,建筑师计算过排水坡度,却算不出百年风雨会在砖缝里刻下怎样的纹路。郭静用陶针在土坯中心扎了个小孔,动作轻得像在给蝴蝶标点:“滴在这里,看它会不会顺着孔隙跑。”
钢笔尖垂落时,赵环的呼吸刻意放轻了。他见过混凝土在模具里凝固的过程,见过玻璃在高温下流淌的姿态,却从未如此专注地等待一滴墨水的渗透。靛蓝色的液珠触到陶土的刹那,并没有立刻晕开,而是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了,在落点处凝成一个饱满的弧,像悬在夜空的星子还没决定是否坠入水面。
“它在试探。”郭静的声音压得很低,“陶土的孔隙比纸纤维更傲娇,得等水分先软化表层。”
果然,三秒后,那滴蓝开始缓慢地扩散。不是纸张上那种均匀的晕染,而是带着某种挣扎的纹路——有的地方突进半厘米,有的地方只蔓延出细细的丝,像水流在干涸的河床上寻找路径。赵环忽然想起自己画的剖面图,那些表示空间层次的线条总是横平竖直,可眼前的蓝却在证明:真实的渗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你看这里。”郭静用指尖点了点土坯边缘,那里有丝极淡的蓝,比中心的颜色浅了三个色号,“陶土密度不一样,吸水速度就不一样。我揉泥的时候,这里多用力捏了两下,孔隙被挤小了,墨水就走得慢。”
他低头,看见她指尖的泥垢蹭在土坯上,与那丝淡蓝形成奇妙的呼应。建筑师的理性告诉他,这是材料密度差异导致的渗透速率不同;可心里另一个声音却在说,这像极了他们某次争论——他坚持美术馆的立柱间距必须符合黄金比例,她却说“好的空间要像两个人并肩走,有时近一点,有时远一点,舒服就行”。
第二滴墨水是郭静滴的。她没用钢笔,而是直接蘸了碗里的清水,混着指尖的陶土末,滴在第一团蓝的边缘。清水渗入的速度比墨水快得多,像给那片靛蓝搭了座透明的桥,让原本停滞的蓝又开始流动,只是颜色被冲淡了,变成雾蒙蒙的青,像水墨画里的远山。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你看,加了杂质的水更容易被吸收。”她用陶针轻轻刮着渗透的边界,“纯墨水太‘硬’,陶土不喜欢。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嘎子剑)的经典小说:《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最新章节...
- 2306992字11-15
- 双修高手玩转都市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台上老菌)的经典小说:《双修高手玩转都市》最新章节全文阅...
- 1046890字12-26
- 快穿:女配的路走宽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天空是寂寞)的经典小说:《快穿:女配的路走宽了》最新章节...
- 1297988字12-16
- 师娘,我真不想下山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冬飞寒)的经典小说:《师娘,我真不想下山啊!》最新章节全文...
- 6941460字06-21
- 魔眼小神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相思如风)的经典小说:《魔眼小神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6090260字04-21
- 仙帝重生之我为主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三千方言)的经典小说:《仙帝重生之我为主宰》最新章节全文...
- 2178057字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