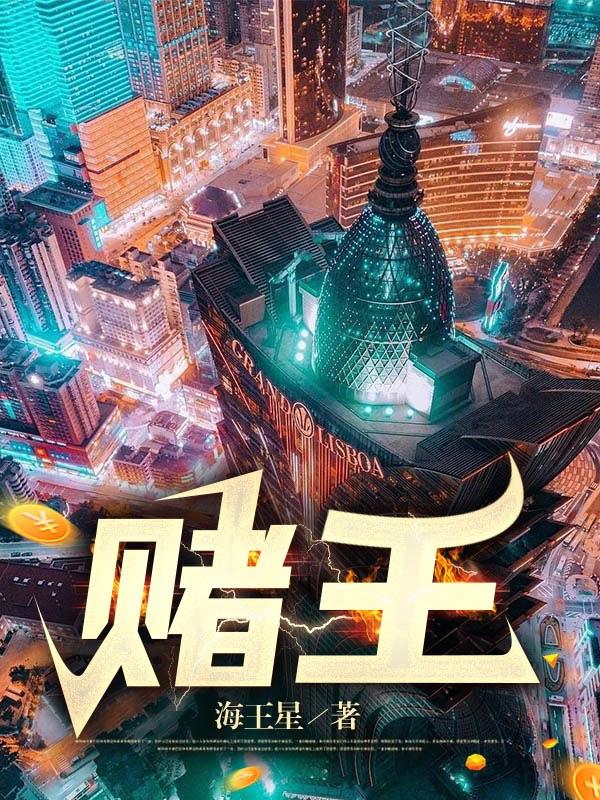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190章 建筑材料的陶艺釉料兼容性测试
控制在0.3毫米,用刮板刮平时的角度保持45度——这些参数都记在他随身携带的黑色笔记本上,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体。
“你做模型时也这样吗?”郭静忽然问。她看着赵环用镊子调整陶片的位置,确保边缘与试块的中轴线完全重合,“连胶水厚度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建筑的容错率在千分之三以内。”赵环头也不抬地回答,笔记本上的铅笔正在记录粘贴时间,“但陶艺……”他顿了顿,抬眼看向郭静,目光落在她耳垂上那枚陶制耳钉——那是她自己捏的小月亮,边缘故意留着不规整的齿痕,“你们允许误差存在,甚至称之为‘手工的呼吸’。”
郭静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在阳光下变得透明:“上次你说美术馆的穹顶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我还在想,要是让我捏一个直径五十米的陶制穹顶,大概会歪到像被风吹过的云。”她拿起一片陶片,让它从掌心滑落到另一只手,釉面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像风铃,“但误差也分两种。有的是失控,有的是故意留出的空间,让材料自己说话。”
拉力试验机的显示屏跳动着数字。等待胶体固化的二十分钟里,赵环打开了另一台设备——盐雾腐蚀试验箱。透明的箱体内,金属格栅上已经放好了三块粘有陶片的铝板。当郭静看到他从试剂瓶里倒出氯化钠溶液,配比精确到每升水含50克盐时,忽然想起上周在他工作室看到的场景:他用同样的专注,计算着混凝土里水泥、沙子和水的比例。
“这是模拟沿海城市的盐雾环境。”赵环合上试验箱的门,按下启动键,细密的白雾立刻在箱内升腾起来,像把陶片和铝板裹进了一片微型云海,“美术馆选址在江边,每年梅雨季的雾气里,氯离子含量会比平时高30%。”
郭静凑近观察窗,看着她的陶片在白雾中若隐若现。那些釉料里的金属氧化物,是她反复调试过的配方:钴料带来的靛蓝,铁元素晕染的月白,还有微量的铜让釉色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紫调的光泽。她从未想过,这些在窑火中绽放的色彩,还要接受如此严苛的“考验”。
“会不会觉得……太残酷了?”赵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不知何时脱下了白大褂,露出里面浅灰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骨处一道浅淡的疤痕——那是大学时做模型时被美工刀划伤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郭静转过身,正好对上他的目光。那双总是带着测量精度的眼睛里,此刻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她忽然明白,他并非只是在执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甄嬛传:从替大胖橘做绝育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静语忘峰)的经典小说:《甄嬛传:从替大胖橘做绝育开始!》...
- 1632074字07-17